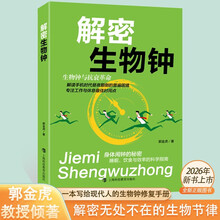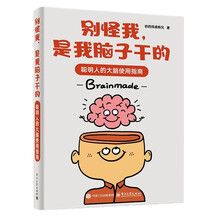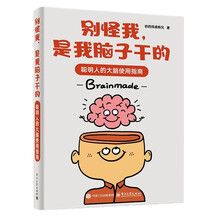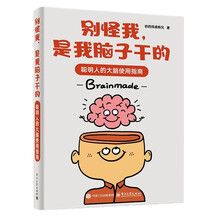这些连续体,或者说某些视觉策略的反复出现,对我们理解人类持久的表达对自然的洞察的方式有深远的影响。我们研究过的这些有深刻洞察力的人能够有规律地利用他们对次序的直觉,这种直觉将自然从最小的单位延伸到最大的整体。我们见证过这样的直觉,在最基本的几何和机械层面上运作的最小的机制,可以引起复杂程度很高的器官形式和功能。相反地,我们也看到,复杂体系如果从整体的层次上来了解,会拒绝分解为小的机能部分。在我看来,“分解论者”和“整体论者”之间的冲突被过分夸大了,因为通过部分来研究整体和把部分作为整体的功能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做是现存的我们了解自然的互为补充的有力工具。从历史上看,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正确性还将持续,因为这两种模式都植根于直觉之中,我们将继续在根本的人类层面上使用这些模式。而且,不管我们让机器为我们做多少工作,最终还是由我们决定做什么、怎样做。很自然,分解论者和整体论者都坚信他们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我认为每个人的气质特点决定着他喜欢哪种方法。
我还认为“分解论”和“整体论”两种方法相互补充的本质超越了人类认知系统的连续性。即使是最标准的新达尔文主义形式中,偶然突变的盲目选择和自然选择机制形态结合的演变不能视为是从物理化学法则的设计限制中分离出来的孤立的操作程序。不过这个十足公式化的表达过分简化了,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完整的模式,就要有一个更细微的差别理论。从地球上生命出现的第一刻起,到高度发达的有机生物体的出现,再到现在,选择机制已经并且将继续充斥着浩如烟海的数据库。此复杂性在于其特性,它以非随机的方式在显著的自我组织中,随时表现着其极端性——以此来实现此效应: 即它在有机和无机形式的每个阶段中都发挥着一个成型作用,包括DNA滋生螺旋的形成。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