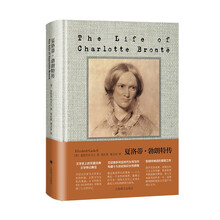蝴蝶晾晒双翼太薄弱,是昙花一现的美丽。当白昼已经过完,依然可期待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夜深长,却有比深长更隽永的芬芳。昙花凋零,自有一室为之储藏清香。清香散尽,还有回忆锁住。所以,即使走到生命尽头,又谁敢说真的过完了一生?诗人会把逝去世界的繁荣带到文字的世界中去,字字留香;生命消亡,亦可化为不灭的精神之光,前行的路途熠熠生辉。
祖母死了,接着,母亲也死了。生命中一个又一个重要的人离她而去。然而,对于亲人,人们往往有太多太复杂太纠葛的情感。你信与不信,亲情也是一种缘。有的缘无限亲近,如同前世就是至亲。比如小萧红与爷爷。有的缘纵使心里亲笃眷念着,面上却总是淡着,仿佛隔着什么。有许多许多的话,还没出口,就被融化在火中,破碎在风里。那个人呵,亲也亲不得,疏也疏不得,想放,却又放不下。有多爱着,就有多怨着。可怨着怨着,却忍不住噙满泪水。他是我们生命里无药可医的伤痛。
当一向严苛的母亲即将离世时,萧红已经懂事了。那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火迅速蔓延开来。这一把火,蔓延到了张家。萧红的母亲姜玉兰,是与萧红截然不同的人。她简直是王熙凤这样的人,是世人眼里精明干练的好媳妇。呼兰张家,虽说世袭繁华,到如今早已呈衰颓之相。之所以还能支撑,全靠姜玉兰的治家本领。
这一年,萧红的二姑家韩家,家财被大火焚烧殆尽,齐齐投奔张家。
张家日子本已只是表皮光鲜,偏偏韩家人好吃懒做,只知抽大烟。姜玉兰眼见自己半生的努力,都要付之一炬,又碍着三从四德的规矩不便抱怨,急火攻心,居然病重不治。
萧红在《情感碎片》中记录了母亲去世的场景:“许多医生来过了……他用银针在母亲腿上剌了一下,他说:‘血流则生,不流则亡。’“我确确实实看到那个针孔没有流血……我站着。
“‘母亲要没了吗?’我想。
“大概就是她极短的清醒的时候:‘你哭了吗?不怕,妈死不了!’我垂下头去,扯住了衣襟。母亲也哭了。
“而后,我站在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我从衣袋里取出母亲买给我的小洋刀。
“‘小洋刀丢了从此就没了吧?’于是眼泪又来了。
“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
眼泪就再也没有流落下来,然而那是热的,是发炎的。但那是孩子的时候。”生离死别,未免会有真情的流露。然而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再也没有比小洋刀更重要的事物,因为那把小洋刀,装载着厚重的母爱。
那母爱,是我们生命的最初所有的财富。尽管母亲有时无暇眷顾,在俗世事物中分给孩子的爱太少。然而,爱终归是爱。
即使后来的继母对萧红,甚至比母亲更为宽容、忍让,然而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打断骨头连着筋,是怎么扯也扯不断的。
经年之后,她或许一边写着:“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是母亲。”一边满怀遗憾,当初为何不紧紧抱着母亲痛哭一场,用眼泪化解怨怼,用最深的爱,照亮母亲来世的路。水里的游鱼兀自沉默,飞鸟与浮云相亲相爱。或许,一切怒放都是凋零的先奏,而一切相聚早已预演着别离。人的一生,有的人能够相伴走一段路,有的人却可以相携走完一辈子的路。对于亲人,再不想割舍,也只能放手。
姜氏是一个极其入世的人,她的世界里不仅仅有萧红。她要将精力照拂整个家族。她并非文化人,亦非闲人,所以分给萧红的爱,自然所剩不多。而脆弱敏感如萧红,所需的爱,却是祖父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关注。祖母死后,萧红吵闹着要搬去跟祖父住。闲来无事,爷孙两人开始读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每次读到“春眠不觉晓”,小萧红就高兴地拍着巴掌,说这声音真好听。“重重叠叠上小楼,几度呼童扫不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