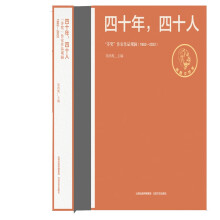诗歌中的叙述并不是要告诉人们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诗歌犯不着去抢占小说的地盘。诗歌中的叙述归根到底只能是一种伪叙述或不可能的叙述。我们不妨说,叙述是为了带出不可能被叙述的东西。这不可陈述的部分就是那些“光斑”,那个“零”。这里边的真实含义毋宁是:零存在于除零之外的所有实数之中,抒情存在于所有的动作(叙述)之内。经过提炼、蒸馏、过滤的纯抒情(比如小孩子那简化式的哇哇大哭)是靠不住的;唯有在令人绝望的、无聊的动作系列中,被其稀释的“光斑”才有意义。因为它既不提纯光斑,也不抛弃光斑。从这个角度看,叙述的90年代并不是对抒情的80年代的彻底背离,而是有礼貌、有风度的继承。80年代那特有的反思在此也有了双重转换:首先是从反思社会转为反思个人生活;其次是把抒情性的愤怒、宣泄溶解到叙述的技巧之内。与80年代有明显区别的是,叙述的90年代把诗歌的目光投向了低矮的、轻声呼叫的,甚至是默默无闻的“现事”和“现时”的凡俗生活本身;宏大、广阔不再作为叙述性的90年代汉语诗歌的背景①。<br> 叙述的20世纪90年代彻底打破了自有新诗以来(不单单是20世纪80年代)建立在人们脑海中那种诗歌纯洁性的神话。由于叙述因素的加入,诗歌显得芜杂多了。在一个有着长期意境追求的诗歌国度,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会让许多人难以接受。本乎于此,许多人抱怨诗歌、远离诗歌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