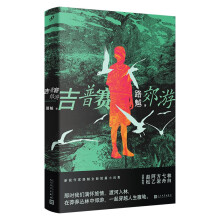故里老屋情
细雨交织成一张朦胧硕大的网,网住我的情感,在一片迷茫之中。倘若我是一只游弋在异乡的小鱼,它的喜怒哀乐也总在故乡这片游不出的海里。这迷蒙的雨丝,为我洗涤着路途上的尘埃,带我走进了生我养我的故土!踏上家乡的土地,第一件事当然是直奔老屋。
那间迎我来到人世间的土屋,仿佛仍弥漫着奶香……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飘雪的寒冬黎明,正忙着操办全家人早饭的母亲独自忍着剧痛,把我生在了老屋灶台下的泥地上。那时,灶膛里的柴火熊熊地燃烧着,满脸汗珠的母亲就着昏黄的煤油灯,烧红了瓷碗碎片,亲手割断脐带的一刹那,她养的那只大公鸡放声高歌,母亲的笑容包裹了我沾满血污的小身体。在我以前的模糊想象里,母亲应该是用一把生锈的剪刀剪断脐带的,但母亲最近才说,其实是摔碎的瓷碗片。我含在眼底的泪水,最终没在母亲面前滑落……
母亲生活中的波澜,似乎与这老屋有着难以说清的牵连。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时常到老屋来做客,因为她表姨的青睐。后来她表姨成为我奶奶。表姨一直疼爱她,表姨说,这囡善良、温厚,谁娶了她,是一生的福气!少年母亲和她的表哥——也就是我父亲,在老屋的后坡种了许多桃树和竹子。他们还在老屋的前庭,开拓了半亩花池,最终贫瘠的生活让它变成了一方菜圃。那时,他们年轻的心里,是否有所期待呢?
表姨早逝,母亲和她的表哥,终日在老屋的厅堂守着她的灵魂,一连几天不曾合眼,表哥心疼她,无数次地给她擦拭眼泪。表妹、表弟们还小,表哥还要读书,母亲从此以后更是常常来老屋帮助做家务。其实,乡亲们,尤其是表哥一家,早把母亲当成了未过门的媳妇!可是母亲自己坚决反对,在她表哥以优异的成绩,成为当时全乡唯一走出深山的大学生时,母亲有了深重的忧虑:自己一个没有条件上学的乡下姑娘,只能一辈子仰望文化的玄妙!
母亲依然常去老屋做农活,但那是在表哥去外地上大学的时候,表哥寒假、暑假归来,母亲总是躲避着他,表哥却追随着她的身影。
母亲、父亲终于领了结婚证,那是在父亲大学时代最后一年的寒假。他得了很重的病,唯一离不开的似乎只有母亲。母亲的善良,让她难以拒绝父亲的依恋。她决心无怨无悔地陪伴他一生一世。尽管后来离异令她万般痛苦,她依然执着地深信父亲的感情不曾改变。
我出生时,父亲在遥远的北方祈祷妻女平安。母亲常常带着一种崇拜一样的感情说:“你父亲真了不起,他能准确地算出你的性别、出生日期,还提前给你取好了名字。”
父亲对我的疼爱是显而易见的。我的名字,突破了家谱排序的制约。爷爷临终时说:“咱家祖辈只有这个女娃走出了大山,也许跟取名字有关系吧?”
我开始蹒跚走路时,每日忙于田地农活的母亲,便把我独自拴在老屋的木床上,她是担忧多动的我,一个人拿着水碗去老井泼水。我在床上玩累了,开始百无聊赖地数房顶的瓦片(其实,我是七八岁时,在小姨的严厉教导下,才学会数数的),我呆望着瓦片,找日光的记号,盼望家里早些回来人。一切都看得烂熟于心了,还没听到家人收工回来的声音,还玩什么呢?我无所事事,干脆滚到床底去找点好玩的吧。床底下黑乎乎的,有些神秘感,我正在寻找,听到母亲进来疾呼我的声音,没有听到过母亲如此腔调的叫声,我故意不开口。母亲着急地寻找,我蜷缩着,屏住呼吸,好想再玩会儿捉迷藏。这时爷爷的声音也变了:“后门是开着的,还不到后山去找找!”随后,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全家人都去找我,后来连邻居都帮着漫山遍野地寻找。无聊的我,竟然悠闲地睡起大觉来,直到我被母亲搂在怀里,她在爷爷的责备声中哭得两眼无神。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乡下常有野兽出入农户。母亲在寻找我的过程中,就像痛失阿毛的祥林嫂。母亲从此把我背进田地,开始日复一日的劳作。直到我五六岁,能独自背起刚刚出生的小弟弟去山上放小鹅。
爷爷在我这次有惊无险的失踪后,似乎也不那么冷落我了,尽管他还会在我不听话地爬上老屋的阁楼掏燕子窝时,向我举起竹鞭;尽管在我偷食邻家的柚子被爷爷发现后,他还是一顿棒打;尽管爷爷给孙女,尤其是我的压岁钱永远少于我的兄弟们……
我的大姑姑生得美丽而端庄,她与同村的阿城两小无猜。阿城从小就不安分,这是爷爷对他的评价。他坚决反对这桩婚事,最后让有情人劳燕分飞,阿城远走他乡,真的不安分地做起了小买卖。后来听说他发迹了,爷爷不屑一顾,倒是对大姑姑的婚后境遇,他深埋着一种疼痛。在爷爷的安排下,大姑姑嫁给了一个深山的石匠。实在没有能力改变困窘生活的姑父,常常因嗜酒而对姑姑拳打脚踢。他们一辈子的争吵,使姑姑很少有干净的脸庞回娘家,但她自己压抑着,从不在外人面前掉泪。爷爷常在夜深人静时,跟奶奶独语。我起夜的时候,见过爷爷对着奶奶的灵牌念叨,泪水纵横。
爷爷对二叔叔也极为严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二叔从书本上看到了用废旧稻草制作沼气的理论,他在老屋后坡雄心勃勃地挖坑,要进行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