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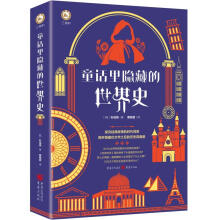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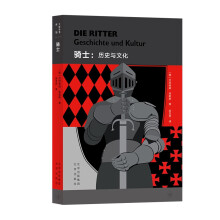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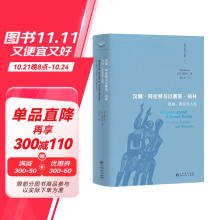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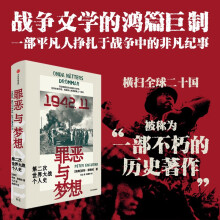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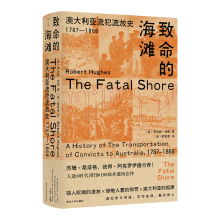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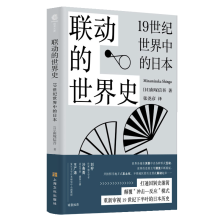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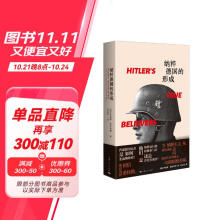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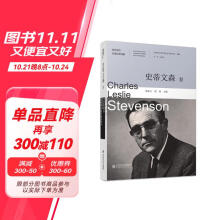

在中国,国家早就沉淀为人们思考不言自明的背景,这本书的启发,并非认识国史的新观点,而是将默认的前提重新问题化的努力,以及新角度对比与观察的刺激。多一双比较与打量的眼睛,就会少几分遮蔽与盲从。
——侯旭东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20年阿尔伯 赫希曼奖获得者的集大成之作,横跨多个学科、于细微处见真章
詹姆斯 C.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以广博而卓越的跨学科研究著称于世。为表彰这种贡献,2020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阿尔伯 赫希曼奖,授予了时年84岁詹姆斯 C.斯科特。与广博的学识相呼应,詹姆斯 C.斯科特在国内学术界和读书界均有着广泛的簇拥,其犹如手术刀般犀利的观点和生动细腻的文风更使其俘获了一众读者。
文明起源的佳作,一本必读的书;2017年《经济学家》最佳历史著作奖获奖作品
本书堪称詹姆斯 C.斯科特集毕生学识,综合考古学、生物学、环境史、人口学等多学科研究而写就的人类早期国家的文明史,这部集大成之作必将成为斯科特又一部重要性作品。
谷物造就国家
说起最早期的成规模农业国家,无论是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埃及、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它们的生存基础都存在着值得关切的相似。简言之,它们都是谷物国家:小麦、大麦,中国的黄河流域则种植小米。后来出现的早期国家也都遵循了相同的模式,当然又有新的谷物加入了这张粮食作物的清单,比如水稻和“新世界”的玉米。就谷物国家这一通例来说,某一局部的例外可能是印加人的国家,他们靠的是玉米和马铃薯,当然,玉米作为税收实物还是最主要的农作物。在所谓的谷物国家中,一两种谷物就能提供主要的食物淀粉,也构成了实物税收的征缴单位,且基于它们编制出支配整个社会的农业历法。对于此类国家而言,冲积土壤和可用的水源构成了它们的生态位,而它们也受限于此。在这里,重点应再一次落到吕西安·费弗尔提出的地理环境“可能论”(possibilism)的概念;对于国家形成来说,这样的生态位(通过挖沟渠或建梯田这样的地貌管理,还可加以扩张)是必需的,但尚且不是充分的。在这种情形中,人口的集中并不等于国家在形成,两者必须要区分开来;正如我们所见,湿地物产丰富,故而可以形成原初的市镇和商业,然而如若没有大规模的谷物种植,就不可能导致国家的形成。
于是问题就来了,谷物为何在最早期的国家中担当起如此举足轻重的角色呢?毕竟,先民们所驯化的并非只有谷类作物——其他农作物,在中东地区尤其是扁豆、鹰嘴豆和豌豆等豆类作物,在中国则是芋头和大豆,也早就完成了驯化。为什么它们无法构成国家形成的基础呢?放宽我们的视野,为什么遍寻历史记录,我们找不到“扁豆国”“鹰嘴豆国”“芋头国”“西米国”“面包果国”“山药国”“木薯国”“马铃薯国”“花生国”或“香蕉国”呢?在上述的培育品种中,就单位面积所能提供的卡路里来说,很多都超过了小麦和大麦,有些甚至不需要投入那么多的劳动力,它们搭配起来或即便是单个品种,就能提供与谷物大致相当的基本营养。换言之,在人口密集条件下提供相应的食物营养,谷类作物所能做到的,许多非谷物的培育品种也能做到,故而也能满足人口密集状态下的农业要件。就土地单位面积所能聚集的热量值而言,在各种农作物中,只有灌溉水稻是远高于其他品种的。
我坚信,要理解谷物和国家之间的关联,关键在于一个事实,即只有谷物可以充当征税的基础,因为它们看得见、可分割、可估价、耐存储、易运输,并且“可定量配给”。其他农作物——如豆类、块茎或淀粉植物,虽然也有某些适于国家所需的品质,但没有哪种作物能像谷物那样,一身兼具所有的优势。如要理解谷物何以独步于农作物界,不妨设身处地地想象你穿越到古代,成为一名收税的官员,你所最在意的,不就是轻松并快捷地占取物资吗?
谷物生长于地上,且大致在同一时间成熟,仅仅这一事实,就会大大减轻收税人员的工作负担。假设军队或者负责收税的官员找准了时间,那么他们在到来之后,就可以一次性地对全部收成进行收割、脱粒,然后打包运走。假如来的是一支敌军,对谷物执行焦土政策也变得轻而易举;敌军可以放一把火,烧光马上就要收获的庄稼,逼得农民要么逃亡,要么饿死。还有更高明的招儿,收税的官员或者敌军可以等着,等到农民把谷物脱粒并且储存之后,再现身把粮仓洗劫一空。比方说,中世纪欧洲实行什一税制,收获时节,农民最好在田地里把尚未脱粒的谷物扎成捆,这样一来,收税官从每十捆中取走一捆就可以了。
在此,我们可以做一比较:前文讲述的是谷物情境,但如若主要种植块茎类的作物,如马铃薯或木薯,农民的情况又会如何呢?块茎类的作物会在一年内成熟,然而块茎在成熟后还可以安全地留在地下,再过一年甚至两年都可以。需要时,农夫可以把它们挖出来,剩下的还就储藏在它们生长的地方,存于地面以下。如果来了一支军队或者收税的官员,想要你的块茎果实,那么他们就得像农夫一样,把地下的果实一块块挖出来,一番操作之后,他们终于收集到一车的马铃薯,但其价值(无论是提供热量还是市场交易)却远低于同样一车子的小麦,而且还容易迅速腐坏。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就明白这一点,他命令自己的子民都种植马铃薯,因为田地里种的是块茎类的作物,那么敌军到来时,驱散农民就不那么容易了。
谷物“长在地面上”,同时成熟,在国家的收税官员看来,其优势是不可估量的,不仅一览无余,而且易于估价。正是这些特征,让小麦、大麦、稻子、小米和玉米成为首选的政治作物。在评估税负时,官员通常会按照土壤品质对地块进行分类,而在知道了某种谷物在相应等级田地上的平均产量之后,他们就能估算出一块地的税额。如果每年的税额都必须要做动态调整,那么就可以对田地进行测量,在即将收成之际选取一块典型的地块,根据这小块地上的庄稼收成来得出该作物年度的预估产量。在下文中,我们也能看到,国家官员还会强制实施某些耕作技术,想要以此来提升作物产量以及实物税额;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有国家要求反复多次的犁耕和反复多次的耙土,前者是为了弄碎土壤里的大土块,后者则是为了利于作物生根,并改进养分输送。归根到底,谷物生长在翻耕后的土壤里,其植株的栽培、庄稼的状况以及最终的产量都更能看得到,也便于评估。在此,我们可以进行比较,一种情形是对谷物庄稼征税,另一种则是对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商业活动进行估价和征税。在古代中国,国家之所以不信任商人阶层,甚至败坏他们的名声,一项理由就在于如下简单的事实:商人的财富不像农民地里的稻子,前者往往是难以识别、易于隐藏,甚至便于出逃的。国家可以对一处市场进行征税,也可以在道路或河流的交汇处收取通行费,因为在这些地方,货物和交易是比较透明的,但问题是,想到要对商人课税,那可就是税吏的一场噩梦了。
谷物的收成最终就是一粒粒细小的粮食,去壳或者未去壳,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事实,然而对于计量、分割和评估来说,却有着巨大的行政优势。谷类作物的粮食,就好像砂糖或沙粒一样,几乎可以无限分割下去,一直到越来越小的颗粒,其重量和体积都可以进行精准的度量,从而符合核算的需要。这样一来,谷物单位就可以充当度量和价值的标准,无论是在贸易还是进贡,都可以以谷物单位为标准,计算其他物品的价值,包括劳动力的价值。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玛王国,最底层的苦力每天所能领取的口粮,就是用斜边碗按量配给的大约两公升大麦,也正因此,这种容器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一类出土物品。
但问题是,为什么世上没有“鹰嘴豆国”或“扁豆国”呢?毕竟,它们也是可以集中种植的营养作物,其收成也是小颗粒的种子,在干燥后易于保存,而且同谷物一样,也很容易细分为小的份额,然后按量配给。说到这里,谷类作物具有一种决定性的优势,就是它们生长期是确定的,也因此几乎是同时成熟。假设你是一位税务官,那么大多数豆类作物在你眼中都有一个问题,它们会不断地开花结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就拿大豆或豌豆来说,它们可以随时成熟随时采摘,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收税的官员如果来得太早,只能看到多数作物尚未成熟;反过来说,如果他们来得太晚,需要纳税的农夫很可能已经处理了大部分的产量——吃到肚子里,隐藏起来,或者卖了出去。在各种农作物中,哪些能让收税官员实现“一站式购物”,最搭配的当然是有确定成熟期的作物。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谷类作物在美索不达米亚早已进行了预先的演化,就在等待国家的形成。至于美洲大陆——除了玉米这个混杂的例子,它既可以随时成熟随时采摘,也可以任其在田间成熟并自然干燥,那里几乎没有生长期确定、可以全场同时成熟的作物,故而也根本见不到欢庆收获的节日传统,而对于旧世界的农业日历来说,这种节日是支配性的。说到这里,我们也不由得推测,为什么会有确定的成熟期,这种作物特性是否源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农耕者有意识的选择,更进一步,若确实如此,为什么先民们不对鹰嘴豆或扁豆进行类似的选择,以形成确定成熟期的特性呢?
即便如此,谷物税负的征收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虽说同样一种谷类作物,一次性栽种,就会同期成熟,但问题在于,季节因素经常会导致种植日期的差异,于是不同地块的庄稼,其成熟日期也会略有差异。为了逃避税收,农民赶在谷物尚未完全成熟前,就偷偷摸摸地收割了一部分庄稼,这种情况也并非罕见。只要有可能,早期国家就会做出尝试,为一个地区规定统一的种植时间。以灌溉水稻为例,国家会选择大约相同的时间,在所有邻近的稻田里放水,只要做到这一点,就等于规定了种植(或者移栽)的时间表,当然更不要忘记这一事实,在水漫田地的条件下,稻米就是唯一可以生长的作物了。
更何况,谷物也很适合进行大宗运输。即便是在如此古老的条件下,运载一车谷物到很远的地方也能有所盈利,其距离能够超过几乎其他任何食物类的货品。而在有水运的地方,大宗的谷物就可以进行长距离运输,如此一来,早期国家所能主宰的农业核心地带也就大大扩展了,国家也因此能从更大的范围内索取税收。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晚期,乌尔第三王朝的一段记载曾提到,驳船载得满满当当,将乌尔地区大麦全部收成的一半都运往王室的仓库。我们在此重申,对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收税官员来说,甚至相关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农业国家如能搭配一段通航的河川或者海岸线,那就可谓是天作之合了。比如说,罗马人曾发现,运输谷物(通常来自埃及)和葡萄酒穿过地中海,其成本大约等于相同货物用马车陆运100英里。
就每单位体积和重量所具有的价值而言,谷物几乎胜过了所有其他的食物品种,而且又相对容易储存,也正因此,谷物是一种理想的税收和生存作物。它可以收割后就放在一边,直到需要时再进行去壳脱粒。它是理想的作物,可用于向劳工和奴隶分配盘中餐,可用于索取贡品,可用于为士兵和驻军提供补给,可用于救济粮食短缺或者饥荒,也可用作敌军围城时的军民口粮。简言之,谷物对于早期国家而言就是其肌体的基础,有国家出现却无谷物的供给,是难以想象的。
在地图上,谷物种植以及农业税的地域,也就是在国家权力的治下,而在谷物不继的地方,也就标志着国家权力由此开始衰退。在早期中国,国家的权力只是存在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内可耕种的地点。这些田地里种植着灌溉水稻,构成了早期中国的生态和政治核心地带,包围着这些中心地区的,是四散分布的游牧、狩猎采集以及游耕的群落,他们居无定所,当然很难对他们课税。他们被定义为“生番”蛮族,是“尚未进入国家版图”的人。罗马帝国纵然野心勃勃,其疆域也从未越过谷物线太多。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罗马人的统治只集中在“拉坦诺”文化区域(考古学家为之命名,所根据的是率先发现该文化器物的瑞士地名),那里人口密度更高,农业生产相对更发达,市镇(所谓的“奥必达”文化)规模也更大;只要走出这一区域,就是“欧洲的亚斯托夫文化”,人烟稀少,或放牧,或刀耕火种。
对于我们来说,上述的对比就构成了一种提醒:原来,最早期的谷物国家就好像是孤岛,在它们的外面是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以及人口。谷物国家的四至,只能局限在一种狭小的生态位,偏好精耕细作的农业。越出它们的地界,就是各种各样可谓“无法占取”的生存活动,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狩猎采集、捕鱼以及海产捕捞、园艺、游耕或者专事畜牧业。
假设你是一位负责收税的国家官员,那么在你眼中,诸如此类的生存形式,在财政上都是徒劳无益的;控制它们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要远远大于从它们那里所能占取的税收。无论是狩猎采集的人口,还是靠海吃海的群落,他们在分布上都是零零散散,而且来去不定,同时他们的“捕获”又是各种各样,且容易腐坏,故而掌握他们的行踪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更谈何对他们征税。说起从事原始园艺农业的先民,早在人类开始种植谷物之前,他们很可能就驯化了根茎和块茎类的作物,对于他们来说,在森林里偷着辟出一小块地,将他们大部分收成留在地下,等到需要时再挖出来,这可不是什么难事。再看看刀耕火种的先民,他们经常会种植一些谷类作物,但在他们的农田上,通常都生长着数十种不同的作物品种,成熟期各不相同。更何况,每隔几年,刀耕火种的先民就会转移他们的土地,时不时还会易地而居。还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口,这种生存方式被认为是由农业发展出的一种分支,他们也是分散且流动的,对于收税官员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奥斯曼帝国是由游牧部落所建立的,统治者就发现,对放牧者征税是极其困难的。于是,他们选择一年一度对放牧者进行征税,就是当牧民停顿下来,照料刚生的羊羔并剪羊毛的时候,但即便是这么做,后勤上也面临着各种困难。鲁迪·林德纳是一位研究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学者,他就曾得出结论:“奥斯曼人梦想着找到一块能安居下来的乐土,从温顺的农夫那里汲取稳定的收入,但对于流动的游牧部落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游牧部落必须要依循气候的微小变动而游移,这样才能找到最丰美的牧草和淡水;结果就是他们总在不断地迁移。”
如此看来,说起不以谷物为生的族群——当时包括的是世界大多数的人口,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实践着各种谋生和社会组织的形式,将税收屏蔽在外:身体的流动、分散、多变的群体和社群规模、繁多且不可见的生存物资、极少的不动产资源。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各自构成了不相往来的小世界。恰恰相反,也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述,他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和贸易。只不过此类往来并非以强力为后盾,主要是以物易物,将所需的物品从一个生态区交换到另一生态区,追求双方的互利。虽然是交易时的伙伴,但这些依靠特别方式谋生的群落,就经常被看作是不同种类的人。比方说,在罗马人看来,所谓蛮族,让其得以区别开来的关键特征就是他们吃奶制品和肉,而不像罗马人那样吃谷物粮食。对于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说,“野蛮的”阿摩利人实在让人忍无可忍,原因是据称他们“五谷不分……茹毛饮血,也不埋葬死者”。
以上所述的各种生存形式,不应当被认为是自给自足、完全隔绝的类别。许多群体都能在不同生存方式之间切换,且他们确实也转变自如,很多时候,他们还会将各种方式混杂起来,故而无法做出简单的归类。而且,我们也不应忽略这种可能性,生存方式的选择经常是一种政治的选择——也就是说,面对着国家,决定将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
前 言
导 论 一个支离破碎的叙事:那些我曾一无所知的
第一章 “驯化”的长历史:从用火、栽培植物、驯养动物,最终是……人类自己
第二章 世界的地景改造:先民的农庄系统
第三章 人畜共患病:流行病的"暴风雨"
第四章 谷物立国:早期国家的农业生态
第五章 人口控制:奴役与战争
第六章 早期国家的脆弱:形为崩溃,实为解体
第七章 蛮族人的流金岁月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温馨提示:请使用太仓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