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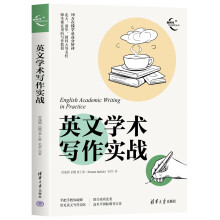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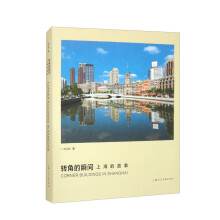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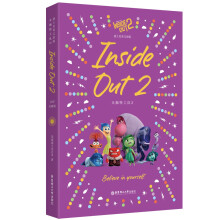






晚饭后他在甲板上待了很长时间,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回到舱里,他还是无法入睡。连这种短暂的休息他也享受不到,这叫他无法忍受。他打开电灯,想看会儿书。有一本诗集是斯温伯恩的著作。他躺在床上翻阅了起来,翻着翻着突然来了兴趣。他把一个章节看完,还想朝下看,可不由又翻了回来。他将书反扣在胸口上,陷入沉思。答案就在这里,这就是答案。奇怪,以前他怎么就没想到过!所有的一切都在此不白自明;他的漫游一直都走的是这个方向,而今斯温伯恩向他指明这就是痛快的出路。他渴望安息,而归宿就在这里。他望了望敞开的舷窗,看到那儿倒是挺宽敞。几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有了喜悦的心情,因为他终于找到了治疗自身病疾的良方。他捧起诗集,慢慢地朗诵那一节:
放弃了对生活的热恋,
摆脱恐惧、告别希望,
我们虔诚地祈祷,
感谢冥冥的上苍,
幸喜生命终有尽期;
死去的不复站起;
纵使疲倦的河流蜿蜒曲回,
总会平安归向海洋。
他又望了望那舷窗。斯温伯恩提供了答案。生活是一场噩梦,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变成了一场噩梦,化为叫人无法忍受的东西。“死去的不复站起!”这一诗行深深打动了他,令他感激涕零。这可是天地之间唯一叫人向往的事情。当生活充满了痛苦,令人厌倦的时候,死亡会哄你沉沉入睡、长眠不醒。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该走啦!
他立起身,抱头探出舷窗,低头望着那浑浊的浪花。马利波萨号满载着旅客,吃水很深,用两手抓住窗子,便可以把脚伸进水里。他可以无声无息地钻入水里,谁都听不见,一朵浪花飞溅起,打湿了他的面孔。他的嘴唇发咸,那味道很是不错。他想着是否应该写一篇绝笔,但随即便一笑置之。已经没有时间了,他迫不及待地要赴黄泉之路。
他熄掉舱里的灯,免得暴露行踪,然后把脚先伸出了舷窗,不料肩膀却被卡住了,于是他抽回身,将一条胳膊紧贴在身旁,再次朝外钻。船体的摆动帮了他的忙,他借力钻出,用手抓紧窗子。双脚一触到海水,他就松了手,落入浑浊的泡沫里。马利波萨号的舷体似一堵黑墙从他身边擦过,星星点点的舷窗里亮着灯光。轮船向前疾驶,几乎未待他清醒过来就把他甩到了后边。他慢慢地在泡沫飞溅的海面上游着。
一条鲣鱼在他白皙的身子上咬了一口,惹得他笑出了声。他身上掉了一块肉,疼痛感才使他想起了投海的目的。他刚才过于忙碌,竟忘了自己的目标。马利波萨号上的灯光在远方愈来愈模糊,而他却在这儿满怀信心地游着泳,就好像一门心思要游到千里开外的最近的陆地似的。
这是一种不由自主地求生本能。他停止了游泳,但一觉得海水漫过嘴,便又猛然伸手划水,让身子朝上浮。他心想这是求生的意志,随即便轻蔑地哼了一声。哈,他还有意志——坚强的意志!只消最后一用劲,这意志就会毁于一旦、烟消云散。
他变变姿势,直立起来,抬头望望静悄悄的群星,同时吐净了肺里的空气。他猛然手脚并用,狠劲划水,将肩膀和半个胸脯都露出水面。这样做是为了能在潜水时多一份冲力。接着,他放松身子,一动不动地朝下沉,似一尊白色雕像没入海中。他有意识地深深吸一口海水,就像一个人服麻醉剂一样。他感到窒息,可这时他的胳膊和腿却乱划一气,把他托出水面,使他又清楚地看到了群星。
他竭力不让空气进入他那快要破裂的肺里,但却徒劳一场。他不肩地心想这是求生的意志在作祟。看来,必须重新换一种方法。他把空气吸进肺里,让里边充得满满的,这样便可以潜得深一些。他转过身,头朝下用出全身的力气和全部的意志往底层游去。他愈潜愈深,睁眼望着那磷光闪闪、幽灵般冲来冲去的鲣鱼群。他一边游,一边希望那些鱼不要来咬他,因为那样会摧毁他紧绷的意志。幸好那些鱼没有咬他,于是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生活赐给他这最后一点好处。
他不断地往下游,累得四肢发酸,几乎动弹不得。他知道自己已到了深处。他的耳膜被海水挤压得发痛,脑袋嗡嗡作响。他的耐受力正在崩溃,可他拼命划动四肢把自己朝更深处送,直至意志动摇,肺里的空气猛然喷射出来。一串串气泡朝上泛起,似小气球般跳动着,摩擦着他的脸颊和眼睛。旋踵而至的便是疼痛和窒息。他眩晕的大脑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这不是死亡,因为死亡没有痛苦。他还活着,这是生存的痛苦,是一种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感觉。这是生活所能给予他的最后一击。
他那倔强的手脚开始击打水,间歇地,有气无力地划动。他愚弄了它们,愚弄了驱使它们击打和划动的求生意志。他游得太深了,它们已无法把他送到海面上去了。他似乎懒洋洋地漂浮在梦境的海洋里。五彩光环包裹着他、沐浴着他,浸透了他的身体。那是什么?好像是一座灯塔。其实,那东西仅存在于他的大脑中——是一道耀眼夺目的白光,闪动得愈来愈快。随着长长的一声轰隆巨响,他觉得自己滚下了非常长的一条宽楼梯。到了底层,他跌入黑暗之中。他明白自己坠入黑暗的世界。就在他明白这一点的瞬间,他的感觉停止了。
温馨提示:请使用太仓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