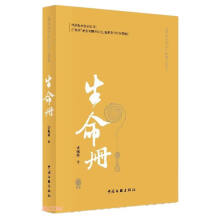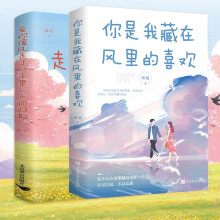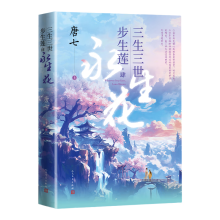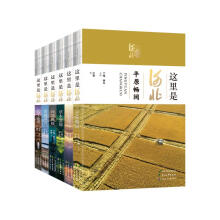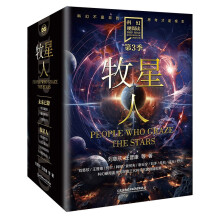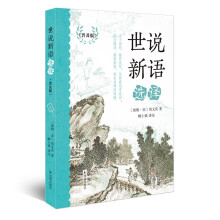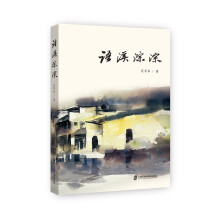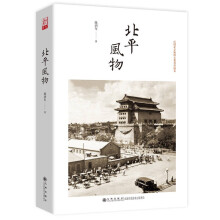《当代文艺评论(第二辑)》:
我刚才说到西湖的会。巴金到了1938年写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二本《春》,里面写了一个故事。觉慧走出家庭,到了上海从事安那其运动。觉新有一天收到觉慧的信,信上说:“我们过得很好,在外面很有意义,最近,我们还到杭州去了一次。”觉新就觉得很安慰,自己的弟弟在外面生活得很好,他知道他去杭州是从事某一种秘密工作。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这秘密工作是共产党地下工作,其实是巴金想象的安那其主义活动,他还是把这件事情写下来了,也就是说,1938年创作《春》的时候,他心里还在想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现实生活中破灭了,他就通过写小说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巴金的小说为什么比别人的小说有吸引力?1930年代,很多年轻人读了巴金的书走出家庭,走上反叛、革命的道路。很多人到今天写文章还写这个。我举个例子,最近读了一本书,叫《青青者忆》,作者是杨苡,翻译家,南师大的外文系教授,已经九十多岁了,她写了这样一本书,把巴金曾经给她的五十多封信都编辑出版。她回忆当年是怎么与巴金通信的,她当年也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哥哥是很有名的翻译家杨宪益,杨苡是杨宪益的妹妹,她当年十七岁的时候,说心里面有一团火,就是想冲出家庭。她爸爸死得很早,妈妈守寡,把他们带大,特别不愿意他们走出家庭,杨苡就给巴金写信,巴金给她回信,说:“你不要这么冒冒失失走出家庭,还是好好读书,读完书再为社会做贡献。”后来她就跑到西南联大去读书,又给巴金写信,当时巴金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把女朋友介绍给她,说:“你们都是小孩子,你们多通通信吧。”后来杨苡和巴金太太萧珊就成了好朋友,一直到萧珊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后来她接着写信,巴金给她回信,这样断断续续,有四十多年。在杨苡跟巴老恢复通信的时候,她碰到了当年中学的同班同学,也是个女生,是班上学生运动最积极的人。两个人碰见后说起,发现两个人当年都给巴金写过信。那个同学告诉杨苡说,她写信给巴金,说她要去参加革命,因为她是孤儿。巴金就鼓励她,后来她就跑到延安参加抗日,又给巴金写信,巴金说:“你继续走下去吧。”可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她被当成特务抓起来了。平反后她的革命情绪一落千丈,说:“我以后再也不记日记,再也不乱写信了。”就这样,她平平稳稳当一个普通干部,一直活到八十多岁。到老了,她与杨苡碰上,说自己也曾经给巴金写过信。杨苡让她再给巴金写信,当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巴金又见了她一次,后来她得癌症去世了。可见,当时和巴金写信的绝对不止一个人,光这个班级里面就有两个女生了。所以巴金吸引别人的,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重要的是巴金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理想因素,尽管理想失败了,信仰也破产了,可是他把对理想的追求写进他的小说里面了,你总会觉得他小说里面的人物和别的人物是不太一样的。
这样一个理想,到了巴金中年以后,慢慢就离开他了。理想总是跟年轻人在一起,当时他四十多岁,功成名就,也结婚了,开始为柴米油盐思考了,他的理想渐渐淡化了。他写了一篇散文《寻梦卜他曾经有一个梦,已经失去了,他还想把它找回来,可是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都看过他1940年代的小说,最有名的是《寒夜》,拍成了很好的电影,但是这里面的理想、激情已经全部没有了。他写一个小人物,很善良,很无奈,生肺病就死了,老婆也离开他了,一点激情都没有。他写完小说,最后一句话是“夜,毕竟太长了”。那个人熬不到天亮就死了。但是1970年代末,这本小说被翻译成法语,在法国出版了,书的腰封上写着: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巴金恍然大悟,原来读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后来他说到《寒夜》的时候,就说,这本书还是有理想的。《寒夜》大家都看过的,最后是一对夫妇分手了,男的因为穷,还有肺病;太太一方面忍受不了婆婆的唠叨,一方面看到丈夫奄奄一息也没有了激情,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就跟着银行内迁,从重庆迁到了兰州。银行经理看上她了,一直追她,用今天的话,就是婚外恋。那个女的很痛苦,到底是跟生病的丈夫在一起,还是跟情人去兰州呢?她在很犹豫的时候.让丈夫给她做决定。丈夫偏偏看到了老婆和别的男人在一起,那个男人长得又英俊,身体又好,又有钱,丈夫痛苦了一阵子后,终于让太太离开他。他的想法是:我生病了,我很痛苦,但是我太太是一个自由的人,她为什么要陪着我死?应该让我太太感到幸福,这样我才能幸福。他最后鼓励太太离开他,后来他太太就走了,一年之后男人就死了。等到太太回来的时候,丈夫已经死了。小说里面是有点批判太太的意思,但是在酷爱自由的法国人看来,这个女性勇敢抛弃了疾病、贫穷,走向爱情和幸福,法国和中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算这样巴金也很开心,觉得自己还是有理想的。但是到了后来,就完全变了。
我看到巴金在《再思录》里有一篇文章,是《(收获)创刊三十年》,里面写道:其实《收获》创办人不是巴金,是他的好朋友靳以。1956年,靳以提出要编一个大型杂志,贯彻当时提出来的双百方针。中国作协也同意了。可是靳以与巴金商量办杂志的时候,巴金只是点点头,说不出好不好。当时靳以充满热情和理想,可是巴金说他自己一点激情都没有了。文章里这样写:“为了体现双百方针,有人建议让他创办一份纯创作的大型刊物,靳以也想试一试,连刊物的名字也想好了。我没有发表意见,说真话,各种各样的大会小会几乎把我的精力消耗光了,我只盼望多放几天假,让我好好休息。因此我没有参加《收获》的筹备工作。靳以对我谈起一些有关的事情,我也只是点点头,讲不出什么。我答应做一个编委。连我在内,编委一共十三人。我说:‘编委就起点顾问的作用吧,用不着多开编委会。’《收获》的编委会果然开得少。”《收获》快出版的时候,靳以找到巴金,说:“还是你跟我合编吧,像以前那样。”巴金想起1930年代他们俩一起编刊物的往事,就同意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