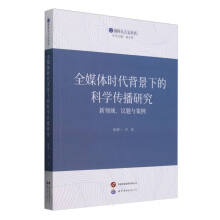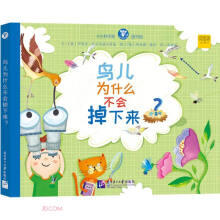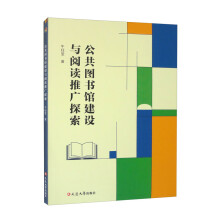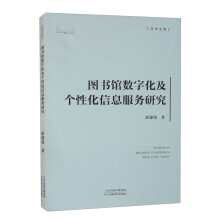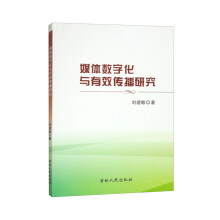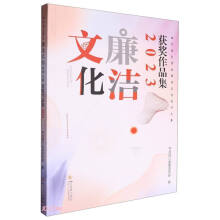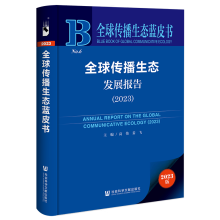《混沌与秩序:新闻伦理探微》:
窃听被引入到新闻采访活动,究竟是扩大了记者的采访权还是损害了其采访权,不能从采访权自身找到答案。权利是多重的,也是多样的。不同的主体(这里指人)之间,许多权利是一样的。不同主体同样的权利,要求权利的主张以不损害他人为底线。假如一个人所主张的权利损害到他人的权利,必然有一方的权利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畴,同时也有悖于权利的伦理准则。更普遍的是,不同主体之间,权利也不同,依然存在某一方的权利受到外来权利侵扰的可能。比如,记者的采访权与被采访对象的隐私权,就属于这种情况。记者的采访活动,被视作代表背后的受众进行提问。这表明,除非特殊环境,采访主要以问答形式进行,因而采访属于记者和被采访对象的信息交流。这样的交流活动,除非记者有意窥探被采访对象的隐私,一般很少能侵害到其隐私。窃听不是采访,而是监听,是靠偷听来记录被窃听对象的言行。监听属于司法部门的秘密侦查手段,其运用也有专门的规定,监听谁、监听的范围、时间和地点,均需要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进行。即便如此,有些监听依然面临诸多争议。举例来说,2006年8月17日,美国底特律市联邦法官泰勒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起诉美国安全部门的境内窃听计划侵犯民权一案作出裁决,认定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授权国家安全局在未经法庭批准情况下,对境内居民的国际通讯进行窃听,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利,违反了宪法中关于三权分立的规定,要求政府立即停止这种窃听活动。虽然这个案件后来在美国最高法院被翻案,法院认定政府为反恐窃听不需法庭授权,但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政府部门的监听只能用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而不具有普适性。
警方和安全部门的监听,是这些部门的特殊权力。这种权力,从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其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有严格的限制,属于有限的权利。过去,在西方,新闻界被誉为“第四权力”,将媒体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现在,这种观念早已被确认为错误,但在某些新闻机构看来,媒体的监督权既是权利更是“权力”。这种观念,在英国的007系列影片《明日帝国》里,反映得淋漓尽致。媒体不满足于报道新闻,还要制造新闻,进而创造他们想要的“世界历史”。这样,采访权从权利错位成权力,无须任何机构授权,便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随意进入他人的私人空间,进行长期窃听。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谁是《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的主谋,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谁下令窃听英国三千多名政治、娱乐名人的个人电话和信箱,下令者和执行者显然并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何不妥。这显然已经是超出了法律层面的问题,属于伦理层面的问题。媒体采访权被滥用,乃权利伦理错位所致,因为媒体从业者自认为他们有权干预社会问题,有义务把那些正在潜伏期的腐败问题和其他明星的丑闻公之于众。这种权利观将媒体的社会责任抬高到与司法部门平行的地位,抹杀了媒体权利和司法权力的界限,若不以纠正,新闻媒体真的将成为独立的“第四权力”。
由此可见,权利意识的浓厚并不等于权利意识的成熟。恰恰相反,对权利认识的偏颇,不仅无助于权利的行使,反而可能导致权利的滥用。窃听丑闻事件让我们认识到,以新闻采访为名进行的窃听,只具备目的善的外表,从采访目的、采访手段到采访效果,都有悖于真正的权利伦理精神。权利的主张必须合法,权利不能以牺牲其他权利为代价。《世界新闻报》的窃听,牺牲的是被采访对象的隐私权。有了窃听,任何人的隐私权均受到威胁。受到威胁的隐私,也就失去了隐私本身。诚如哲学家弗里德所说:“当且仅当一个人能控制关于自己的信息时,它才拥有隐私。”真正的权利,需要权利主张者能为自身提供获得其合法利益所需求的一切。隐私是公民正当的基本权利之一,即便是可能存在违法嫌疑的隐私活动,也只能由法定的机构进行监控。显然,新闻媒体并不属于这样的法定机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