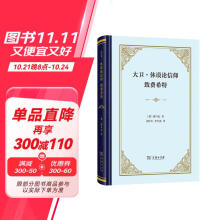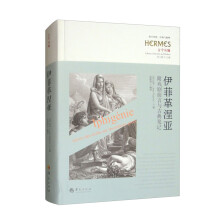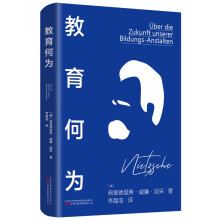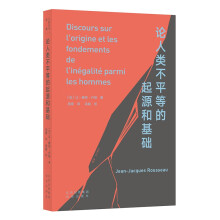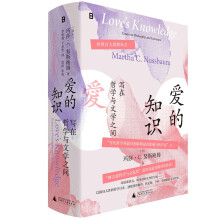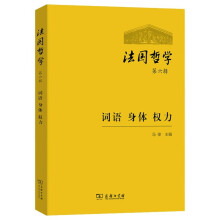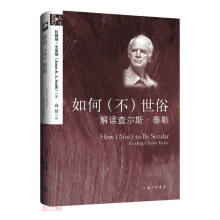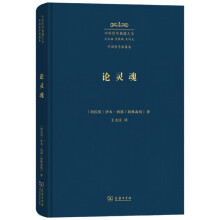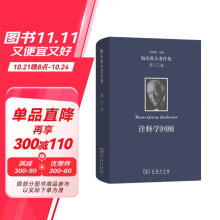《清华西方哲学研究(第四卷 第二期 2018年冬季卷)》:
我们再来看看“满足合理的预期”。我们已经给出了对这个“贫乏反驳”的回应。斯多亚学派会说,“生活的美好流淌”确实包括了满足所有合理的预期,因为你能够合理预期的东西就是实现你能力范围内的好东西。培养你的理性,实现与你周围环境的和谐,就是合理的预期。想要更多就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积极的情感”。这触及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无法在这里很深入地讨论。我们只需要指出,斯多亚学派认为“愉悦”“快活”“自信”之类的心灵状态是“最终的好”,也就是说幸福的组成部分。①这么看来,他们并没有忽视“积极的情感”,而是主张那是对伦理德性(也就是能够很好地进行推理的性情)的分享或者是伦理德性的副产品。斯多亚学派的智慧之人,不像那些对幸福持有错误理解的人那样,并没有不当的情感。但是他对于世界的看法,并不像斯多亚学派说的那样是从世界“退却”。相反,因为他牢固地占有一切好的东西,他从“生活的美好流淌”中获得正面的情感。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虚伪反驳”。通过前面的论证,“与自然一致的生活”或者“生活的美好流淌”与理性的完善是一回事,它们也构成了伦理德性。斯多亚学派的智慧之人因为他们的德性,会做一切kathekonta,也就是遵循一切恰当行动的规则,而且在他这样做的时候,完全理解这些是对于他这个理性的存在提出的无条件的要求。他会照顾自己的家庭,服务于自己的国家,遵守自己的承诺,等等。因为理性告诉他,他应该做这些事情。他为了这些事情本身做它们,将理性要求的知识应用于实践。
不可否认,在这种对人的伦理要求与康德理解的道德的直言律令之间,有某种相似性。但是这个相似性意味着在这两种道德理论之间有什么深刻的联系吗?在康德看来,“培养理性对于产生一个本身就是好的意愿来讲是必须的,而这在很多方面会妨碍幸福的实现,这与自然的智慧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相反,自然不会错失自己的目的”。①康德可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他看来,人性是双重的,从物理的角度看,人的目的是幸福/快乐,但是人还有一个更高的理性的自然,它的目的是道德。
如果我们理解无误,那么斯多亚学派不承认这种二元论。根据他们的理论,充分发展的人类自然完全是一元的。在我们从婴儿发展到成年的过程中,理性调整着我们的关切、价值和导向,并不是抛弃最开始的追求,而是在那上面添砖加瓦。充分发展的人类自然,虽然不同于不成熟的早先阶段,但依然是自然现实中完全自洽的一部分。自然法则在人类自然上的应用与在其他方面的应用完全一样。
福希纳曾认为,斯多亚学派预见了康德,因为他们区分了习俗中的好(比如健康)与道德上的好(也就是德性),认为这两类好对人来讲都是自然的,但是只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好,并且与人的理性自然相一致。他因此推论说,斯多亚学派就是康德的雏形,康德所说的幸福,在两个理论里面都位于理性的范围之外;而斯多亚学派所说的幸福,实际上类似于康德所说的更高自然的生活。
假如斯多亚学派像康德一样认为成熟的人有两重自然,并且说只有一个自然(也就是理性的自然)在伦理领域之中,那么福希纳的立场就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是斯多亚学派的理论。相反,我们看到,他们认为,人只有一重自然,也就是理性的自然,它既有可能符合,又有可能不符合理性的标准。“虚伪的指控”错误地将斯多亚学派真正的幸福论当作了某种对义务论的错误命名。③斯多亚学派要为自己的伦理学辩护,会这样说:当然,我们的伦理学是一个系统,它将好完全建立在理性的良好运转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