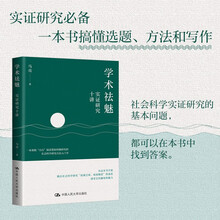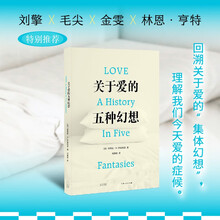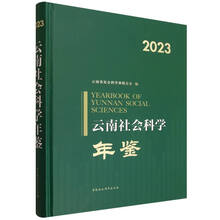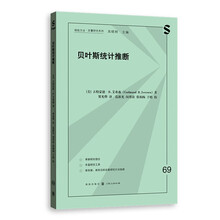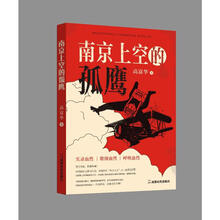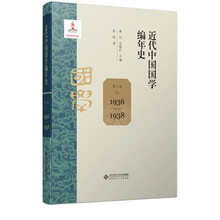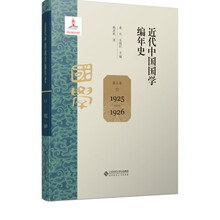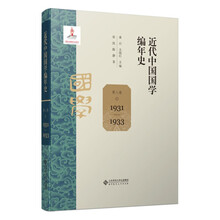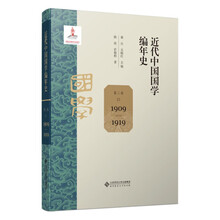《规范性问题和中西哲学:《思想与文化》第二十三辑》:
4.当成真(holding true)和做成真(making true)之间的关系:揭示一个儒家一孟子式范例
甚至在人们已经认可柏拉图原则的规范性基础之后,他们仍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应当采用这个而不是那个特定的原则来作为一个阐释的(与之相对的,例如,教育的)规范性原则。我们创制及贯彻这样一个规范性原则的自由度有没有任何自然而终极的约束?如果有约束的话,那么这种约束是否应当来自人们现有的平均心智状态或其一般水平?换句话说,就一个规范性原则而言,是否存在一个描述上的准确性或似真性问题?
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规范性的规则,其唯一的目的只是要求服从和遵守。比如,一种有关工作制服的规则。规则制定者不必在意那些被要求服从规则者是否,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规则所要求的行为;在此唯一需要关心的是此后这些行为的出现,不论他们为了遵守规则要付出多大努力。很明显,在这些规则中不存在描述的精确性问题,即这些规则的应用对象的现状(statusquo)或常规状况对规则本身的成立与否并不构成约束。但值得注意的是,任何规则制定者必须假定,规则的应用对象能够达到规则的要求①,或者是他们能够朝着那个尚未达到的方向去改变自身;否则的话,制定这样一个规则就没有意义。简言之,除了潜能性或(一种狭义上的)“可完善性”乃其必要条件之外,人们的现状并不是这类规则的考虑因素。
然而,当谈及阐释领域时,事情就变得大为不同了。由于阐释的目标在于搞清某个现存和既定的现象,它的内核自然是以真相为依归的描述性。那么,在一个关乎客体实质的阐释当中,对于一个以遵守服从为导向的规范性内容而言,哪里还为客观描述留下空间呢?因而,“阐释的规范性原则”的提法不免会产生某种悖论感:一方面阐释要求关于被阐释之人现状的真实陈述,另一方面该原则的规范性则要求阐释对象对某一标准的适应或服从。这后一方面所对应的特殊的(即批判的)规范性要求预设着阐释对象作出改变的潜能性。人们如何能够无矛盾地将这两个对立的要求并置一处呢?
理论上说,对某一对象进行客观阐释的尝试应与对同一(所谓非理性)对象进行理性批判的尝试分开来。倘若这两种尝试在人类实践的现实中是互相分离的,则无必要去讨论批判性阐释及由此产生的任何悖论。然而不幸的是,现实的诠释学境况与此理论图景相去甚远。在戴维森关于非理性悖论的表述中,以及他在别处的一些饶富辩证意味的评论中,他对辨识非理性的理性背景之必然性的强调似乎产生于一个直觉:即不大可能将阐释从整体理性背景下对非理性的规范性批判中分离出来。这种观点是,如果没有将大量的理性属性归之于阐释对象,就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批判性阐释凸显出来。
在某些层面上,也许仅仅只有一种可能的理解模式——这种批判式理解是由基本的理性规则建构和规定的,对于这些基本的理性规则,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其作为具有思想的必要前提条件。正如戴维森自己提及的那样,“把至少某些非理性确认为内在不融贯……并不是去解释,甚至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去描述这些心理状态;相反,它使描述和解释的难题变得几乎没有可能解决”。在这里,“描述和解释”指的是那些欲摆脱像柏拉图原则这类理性规则而在理解上做出的努力。对于人类行为的一些有意义的理解来说,如果某些理性规则和原则是必要的根据或不可或缺的成分,那么一个明显的暗示是,它们接近正常人或其潜能得以实现的正常条件,或者说至少不会偏离得太远。然而另一方面,若要问这些规则和原则于现实描述的精确性要达到何种程度才会对整体的人类规范性实践最完美或长远最有利,则似乎没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更可信的事实是,大多数这类原则不是任何个人刻意设计或自觉选择的产物,而是长期进化过程中人类适应种种环境(包括自然变化,以及文化与自然的相互影响)的某种“社会积淀物”。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