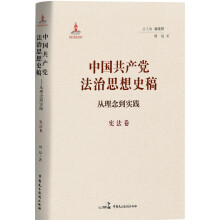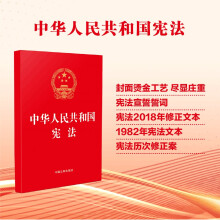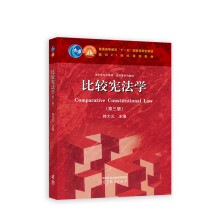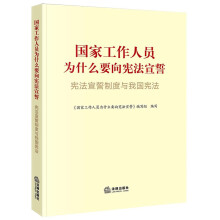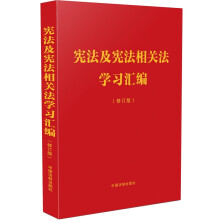《宪法与实在宪法/法哲学名著译丛》:
美国的联邦国家史发端于第一类实质内容,其被缔造的意义是纯技术性的。众所周知的是,当时的宪法不含基本权利。尽管龉龃不断,但政治精神的统一性起初竟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根本无须表述出来(在门罗主义中是特意相对于欧洲被明确表述出来的),且宪法上的共和国宪法的保障(第4条第4项)只是一种保护承诺,而非成为共和国的强制性要求(《魏玛宪法》第17条就有此含义)。只到19世纪才发生了围绕着这个国家特殊民主精神的斗争,而自《第十五宪法修正案》起,这个国家才成为了基于宪法为特定观念原则所决定的国家。
瑞士的联邦化道路则与之相反。瑞士的联邦国家是一种观念纲领在国家法中得到确立的形式,也即在分离主义联盟战争(Sonderbundkrieg)中大获全胜的自由主义观念纲领。健全的保护少数派的机制以及人口稀少的少数派州在联邦院中不成比例的投票权重对此纲领有轻微的弱化作用。与之相反,1874年的改革则是由技术性要素所主导的。
在此观察视野中,人们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俾斯麦所缔造的帝国的根本特性。
“保罗教堂宪法”意欲缔造同时满足技术上(特别是在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行动能力上和精神上的三种要求的民族国家,“俾斯麦宪法”仅将自身定位于技术性问题的解决。
首次帝国议会上的皇帝致辞就已经明白无疑地宣明了这一点。关于政府的统一问题,皇帝致辞中有这样的表述:“在既往情况的基础上,通过一定数量特定的、有限的但极为重要的制度,而且这些制度不仅必须具备直接的可能性,也必须具备毫无疑问的必要性。”这就意味着各个成员国政府的统一仅意味着一种限制,而此种限制的正当性在于,“就捍卫和平、保障国土安全和促进居民福祉这些目的而言,各个成员国做出一定的牺牲是不可或缺的”。①
《帝国宪法》的特性本身也与之相符。当代民族国家在宪法中用以表明自身属性的一些仪式性做法,例如壮怀激烈的序言,②挟着宪法政策上的某种箴言的威严而对基本属性、国体所作的表述,以国徽和国旗作为自身的象征(在第55条中完全被处理’成一个次要的技术性问题),通过基本权利清单宣告信奉现代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基础③,针对所有这些,“俾斯麦宪法”未置一词。这一新生的政治整体明确地以“围绕着国防、贸易、其他在宪法开头段落中提到的对象的政治性目的联盟的形象示人,而非作为一种常态的统一体以及一种精神上的民族统一体”④。此种联盟的机构组织也与之相适应:仅仅是出于此种目的,邦联大会(Bundesversammlung)和主席团(Prasidum)被直接从法兰克福承继过来,作为联邦和帝国的两个最高机关,帝国议会(Bundestag)是唯一新设的机关。人们完全可以将这样一种组织结构理解为曾经一再被要求的对邦联执行机制改革呼声的满足,或者说是对邦联技术性改革纲要的满足。即便第三个机关承载的民族统一的激情笼罩着从邦联议会移植过来的领域,主席团变成了皇帝,且因之被提升为最有力度的民族性的整合要素,宪法也仿佛对此视而不见。“俾斯麦宪法”没有创设新帝国的主权者,且将关于皇帝的规定置于没有任何色彩的“主席团”的标题之下,而“主席团”在顺位上也只是排名第二的帝国机关。而且,“俾斯麦宪法”也听凭人们指责国家法背弃了凡尔赛宫的宣言。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