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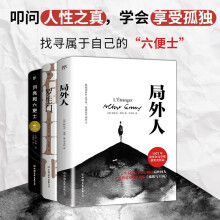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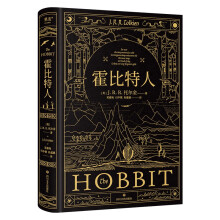




圣诞树和婚礼
——摘自一个不相识的人的手记
前几天,我看了一次婚礼……啊,不!我不如跟您谈谈那棵圣诞树。那次婚礼很出色,我非常喜欢;不过,另外有一桩事情更其出色。不知怎么,我眼看着婚礼,心里想起了那棵圣诞树。事情是这样的:不多不少五年前的除夕,有人请我参加一次儿童晚会。主人是一位商界名人,他关系众多,交游广阔,又有一些打算,因此可想而知,这次儿童晚会不过是个幌子,好让那些父母们借此聚在一起,可以天南地北、无伤大雅地随意谈论种种他们有兴趣的话题。我是个不相干的人,没有什么可谈的,因此我可以说是相当自由地消磨了这一晚上。那儿还有一位先生,看样子出身门第都很平常,但是他像我一样,也碰巧参加了这次家庭欢聚……他第一个引起我的注意。这人是瘦长个子,神态十分严肃,衣着十分合身。然而可以看得出来,他毫无在这家庭欢聚中寻找乐趣的兴致;他只要一躲到哪个角落里,就立刻收起笑容,两条又浓又黑的眉毛皱了起来。整个晚会上,除了主人以外,他没有一个相识的人。他分明是无聊得可怕,可是他始终鼓着勇气,装出一副十分快活舒心的样子。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是从外省来的,他在首都有一件紧要而又棘手的事情要办,他带了一封介绍信见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也就毫不热情地予以照顾,为了不失礼仪,还请他来参加自己的儿童晚会。他不玩纸牌,人家也不敬他雪茄烟,谁也不跟他攀谈,多半是凭那一身羽毛老远就认出了这只鸟儿,这一来,害得我注目的这位先生一双手不知搁哪儿好,只好一晚上摸他的连鬓胡子。那连鬓胡子长得也确是十分好看。可是他摸胡子摸得太热心了,谁看了都不免要想:大概是先有这连鬓胡子,后有这位附属于这胡子的先生,为的是好抚摸它们。
这个人参加主人(他有五个养得肥肥胖胖的孩子)的家庭欢聚的情形就是这样。除了他,还有一位先生引起我的注意。他可是和那一个大不相同。这是位有来历的人物。他名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晚会上的贵客。他对主人的态度正好跟主人对待那位摸连鬓胡子的先生的态度一样。主人夫妇对他说了无数的殷勤话,巴结他,劝他喝酒,照料得无微不至。他们向他引见自己的客人,却始终不引他去见别人。当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谈到这个晚会,说他难得有机会这样愉快地消磨时光的时候,我看到主人的眼里闪着泪花。在这样一位人物面前,我感到有些惶恐,因此,在欣赏了一番孩子以后,我退到一间空无一人的小客室里,在那座几乎占整个房间的一半的花亭里坐下来。
孩子们全都逗人喜爱得出奇,他们不管家庭女教师和做妈妈的如何告诫,坚决不愿意学那些大人。一眨眼间,他们把圣诞树上的糖果抢了个精光。他们还没有知道哪一件玩具归谁,就已经把一半的玩具拆毁了。有一个黑眼睛、一头鬈发的男孩特别逗人喜欢,他老想用他的木枪打死我。然而他的姊姊,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却更其引人注目。她美得像一个小爱神罗马神话中司恋爱之神。绘画及雕刻中常表现为裸体的美少年,生有双翅,手持弓矢。,文文静静,仿佛在想心事;她脸色苍白,一对大眼睛微微鼓起,若有所思。她大概是受了孩子们的欺负,因此撇下他们,来到我坐的这间客室,在一个角落里玩她的玩具娃娃。客人们怀着敬意向她的父亲,一个有钱的包税商,指指点点。有人小声说,他已经拨出了三十万卢布作为她的陪嫁。我转过身去看那些好奇地谈论着这件事的人们,我的眼光落到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身上,他手抄在背后,微歪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听这些先生们闲聊。随后,我不能不佩服男女主人在给孩子们分送礼物上用的那番心机。那个已经有三十万卢布作陪嫁的小姑娘得了那个最贵重的玩具娃娃。接下去分发的礼物,随着这些欢天喜地的孩子们的父母的等级逐步降低,价值也越来越低。到了最后,那个排在末位的孩子,一个身体瘦小、脸长雀斑、红头发的十来岁的男孩,只得了一本故事书。这书讲自然界的壮观和深受感动的热泪等等,却没有图画,甚至连每一章开头和结尾的装饰画也没有。这孩子的母亲是主人的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一个穷寡妇。孩子受尽欺凌,吓破了胆。他穿一件用劣等黄色土布做的短上衣。他得了那本书以后,在其他的玩具周围走了好久;他非常希望跟别的孩子一块儿玩,可是他不敢;他明明已经感觉到并且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我非常喜欢观察孩子,对他们在生活中的初次独立的表现有着极大的好奇心。我注意到那个红头发的男孩被别的孩子的值钱的玩具吸引到了如此地步,他决定低声下气地接近他们;特别使他着迷的是演的一场戏,他觉得自己一定得在那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露出笑容,跟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起来,他把自己的苹果给了一个脸庞浮肿的小男孩子(那孩子把得到的小礼物用手帕包成鼓鼓的一包)。他甚至把一个孩子背在背上,为的是演戏时不至于让人轰出去。可是过不了一会,一个淘气的孩子狠狠地揍了他一下。他想哭又不敢哭出来。这当儿,他的妈妈,那位家庭女教师来了,她嘱咐他别去打搅别的孩子们玩儿。这孩子就走进那间客室,前面说的那位小姑娘正在那儿。她让他跟她在一起,于是两人就十分起劲地动手给那个贵重的玩具娃娃打扮起来。
我在攀满常春藤的花亭里坐了有半个钟点,听红头发的男孩跟那有三十万卢布作陪嫁、这时正忙着侍弄娃娃的小美人儿叽叽咕咕讲话,听得几乎打起盹来。这时候,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忽然走进房间来了。他趁孩子们争吵引起的一场热闹这个机会悄悄溜出了大厅。不多一会儿以前,我看到他同刚结识的那位未来的有钱的新娘的爸爸极其热烈地谈论某一种职务和另一种职务相比的优越性。现在他却站着想心事,扳着手指头似乎在计算什么。
“三十……三十万,”他小声念叨着,“十一岁……十二……十三,这样下去,过五年就是十六岁!假定年利四厘——一年一万二,乘五,就是六万,再拿这六万……嗯,假定五年之后一共是四十万。是啊!这……不过,他不至于只肯给四厘,那骗子!他可以放到八厘或者九厘。嗯,五十,就算是五十万吧,至少这是拿得稳的;嗯,外加嫁装,哦……”
他想完心事,擤了擤鼻子,正想走出房去,忽然一眼看到那位小姑娘,就停了脚步。我在那些盆景后面,他看不见。他的神色看来十分紧张。也许是那番计算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也许是什么别的原因,反正他搓了搓手,再也站不住了。在他停下来,又用果断的眼光看那位未来的新娘一眼的时候,那种紧张不安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刚要往前走,又停住,往四下里望了望。然后他似乎觉得自己在犯罪似的,踮起脚,向那孩子走过去。他微微笑着走到孩子面前,弯下腰,亲了亲她的脑袋。她没有料到有这一下,吓得叫了一声。
“好孩子,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小声问,手拍着小姑娘的脸蛋儿,眼珠子骨碌碌地东张西望。
“我们在玩儿……”
“啊?跟他在玩儿?”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瞟了那男孩一眼。
“你到大厅里去,乖孩子。”他对他说。
男孩睁大眼睛望着他,一声不响。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又往四下里扫了一眼,又对小姑娘弯下腰去。
“好孩子,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是娃娃么?”他问道。
“是娃娃。”小姑娘回答,她皱起眉头,有点儿胆怯。
“娃娃……好孩子,你知道你的娃娃是用什么做的么?”
“不知道……”小姑娘小声回答,一直低下头去。
“是用破布头做的,小宝贝。你到大厅里去,孩子,到你的伙伴那儿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狠狠地瞪了那男孩一眼,说。小姑娘和男孩皱起眉头,彼此拉着手不放。他们不愿意分离。
“那末你知道人家为什么送你这个娃娃么?”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问道,他的嗓音越压越低了。
“不知道。”
“那是因为你这一个星期来一直规规矩矩,挺招人疼。”
这时候,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紧张不安到了极点,他对四周望了望,把嗓门压得更低,终于用一种让激动和焦急的情绪憋得几乎听不出的声音问道:
“亲爱的小姑娘,要是有一天我到你爹妈家里去做客,你会爱上我么?”
说完这句话,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又想吻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可是那个红头发的男孩看到她简直要哭出来了,就一把抓住她的手,而且由于对她满腔同情,呜呜地哭诉起来。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这下子可真的生气了。
“去,离开这儿,去!”他对男孩说,“到大厅里去,到那儿去,到你的伙伴那儿去!”
“不,他用不着走,用不着走!您走开吧,”小姑娘说,“别管他,别管他!”她说,几乎要哭出声来了。
有人在门口发出声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吃了一惊,立刻伸直他的一表堂堂的身躯。但是那个红头发的男孩吓得比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还厉害,他丢下了小姑娘,贴着墙壁,悄悄地溜出客室,进了餐厅。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为了不让人疑心,也走进了餐厅。他脸红得像龙虾,好像问心有愧似的对镜子望了一眼。他大概觉得自己不该那么急躁,那么沉不住气,因此心中懊恼。也许,他开头屈指计算了一番以后,兴奋过度,神魂颠倒,完全入了迷,这才会不顾自己是何等尊贵、何等稳重,决定像孩子一般行动,直接去紧紧抓住他的对象,虽说那对象要成为真正的对象,至少还得过五年。我在这位尊贵的先生之后走进餐厅,看到了一件怪事。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又气又恨,脸涨得通红,在威吓那个红头发的男孩,孩子从他跟前只管往后退,吓得不知往哪儿跑才好。
“去,你在这儿干什么?去,没出息的小东西,去!你是到这儿来偷果子吃的,对不对?你是到这儿来偷果子吃的?去,没出息的小东西,去,拖鼻涕的小家伙,去,到你的伙伴那儿去!”
孩子吓昏了,一时走投无路,就决定往桌子底下钻。这一来,他的压迫者激愤得无以复加,掏出自己的长麻纱手绢,抽打起桌子底下的那个一声不吭的孩子来。这里必须交代一下,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有些发胖,他保养得很好,红光满面,身体结实,大腹便便,再加两条粗大腿,总之,正是俗话说的那样,又圆又结实,活像一颗核桃。他淌着汗,气喘吁吁,脸红得吓人。末了,他的一肚子怒气,也许还有妒意(谁知道呢?),几乎到了使他暴跳如雷的地步。我不由得哈哈大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转过身来,虽说他威势显赫,此刻却也羞愧得无地自容。正在这当儿,从对面门口进来了男主人。孩子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擦干净自己的胳膊肘和膝盖。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原来手抓着一个手绢角,这时候赶紧把手绢凑到鼻子上。
主人眼看着我们三个,有些莫名其妙;不过他是个阅历很深、凡事又很认真的人,因此他立刻利用了这个和他的客人面对面的机会。
“我向您冒昧提出请求的……”他指着红头发孩子说,“就是这个孩子。”
“噢?”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应声说,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他是我孩子的家庭女教师的儿子,”主人用恳求的语气接着说,“那是个穷苦的女人,是个寡妇,她的丈夫原来是个正直的公务员;因此……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如果可能的话……”
“啊,不行,不行,”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急急忙忙嚷起来,“不行,请您原谅,菲利普·阿历克赛维奇,这绝对不可能。我已经问过了,没有空额,再说,即使有一个空额,也早已有十个孩子等着补缺了,他们有比他大得多的权利……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真遗憾,”主人也说,“这孩子又老实又安静……”
“依我看,他是个捣蛋鬼,”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神经质地牵动嘴巴,回答,“去,孩子,站在这儿干什么,到你的伙伴那儿去!”他转身向着孩子说。
这时候,他似乎忍不住地用一只眼睛瞟了我一眼。我呢,也忍不住当着他的面哈哈大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马上扭过头去,用有意让我听见的相当清晰的嗓音问主人,这个奇怪的青年人是谁?他们小声说了几句,走出了房间。我随后看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边听主人说话,一边露出一副不相信的神气,直摇头。
我笑够了以后,回到大厅里。这位大人物让各家父母、男女主人围着,正在那儿跟一位他刚被引见的太太起劲地讲什么。那位太太手牵着那个小姑娘。十分钟以前,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在客室里同这小姑娘有过一场风波;此刻他却眉飞色舞地极口称赞这位小宝贝的美丽、才能、优美的神采、娴雅的举止。他分明是在她妈妈面前献殷勤。那位母亲听他说话,欢喜得几乎掉下泪来。做父亲的嘴角泛着微笑。主人看到这皆大欢喜的光景,自是高兴。甚至所有的客人也有同感,连孩子们也停了游戏,免得妨碍这场谈话。整个大厅都充满了虔敬的气氛。我随后听得那个美丽动人的小姑娘的妈妈打心底里受了感动,用一些仔细斟酌过的词句请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赏光到他们家去作客,这对他们将是破格的荣誉;我听见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带着一种由衷的欢喜接受了邀请;在客人们彬彬有礼地向各处散开以后,我又听得他们彼此用十分动人的言辞对包税商夫妇,他们的女儿,特别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赞不绝口。
“这位先生结了婚没有?”我几乎是大声地问我的一个相识的人,他站的地方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比谁都近。
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没有!”我的相识回答,他对我故意这样不知趣的发问,打心底里感到不痛快。
不久以前,我走过***教堂,那里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使我感到意外。四周的人们都在谈论这次婚礼。这天天色阴沉,而且已经下起雨夹雪来;我跟在人丛后面挤进教堂,一眼看到了新郎。他是个脑满肠肥、大腹便便、身材不高、胖胖墩墩、穿得极其华丽的人物。他跑来跑去,张罗忙碌,发号施令。末了,人丛中纷纷传言,说是新娘到了。我好不容易挤过人群,看到了一位绝色美人,她看来还只进入她的妙龄的第一个春天。但是这位美人面容惨白,神情悒郁,一副神思恍惚的样子。我甚至觉得:她眼圈红红的一定哭过不久。她的脸部每一线条的古典式的严整赋予她的美丽一种端庄肃穆的神态。然而透过那种严整端庄的气象,透过那种悒郁的神情,依然可以看出最初的童稚的天真无邪的容颜;似乎有什么稚气到了极点的、没有定型的、年轻的东西在默默无言地为自己恳求哀怜。
有人说:她刚满十六岁。我仔细看了看新郎,突然认出他就是我整整五年没有见面的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我又端详了她一番……我的天!我赶紧挤出教堂。人丛里有人说,新娘十分有钱,新娘有五十万卢布的陪嫁……还有那么多的嫁装……
“算计得倒是真精明!”我心里想,一边往街上挤去……
……
圣诞树和婚礼
白夜
温顺的女性
温馨提示:请使用太仓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