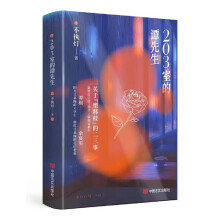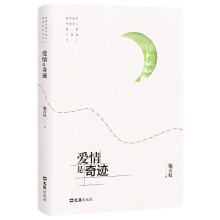离婚身体很受伤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把它走完。对于男人,受伤是一种荣耀;对于一个身为单亲爸爸的男人,与生活和命运的抗争,绝不在乎很受伤。大老爷们向前冲!”
如此励志的句子,是我发在当日的微博上的。而我真的受伤了,既不是见义勇为,也不是遭人报复,我是纯属自残。
这一切源自我想在泼猴面前展示作为他老爸的我的无敌英姿,却不料,偷鸡不成蚀把米,我把自己伤到了。泼猴是我儿子,今年六岁,由于生日赶在了十月份,所以还在幼儿园大班待着。
恰逢周日,我和泼猴正在广场闲逛。看到一个个下到四五岁、上到十四五岁的孩子在一种叫扭扭板的流行器械上正潇洒展示美妙身姿,泼猴鼓足勇气对我说:“二师兄,我想买个扭扭板。”
为了试验一下这玩意儿的安全性,我和一个跟泼猴差不多大的孩子商量了半天,终于让那孩子同意让我这“高龄儿童”用他的扭扭板先在泼猴面前展示一下他老爸的英姿。踏上一只脚,感觉还不错,于是我便放心地踏上了第二只脚,顺便扭动了一下我那水桶腰—出事了。
先是刺啦一声,扭扭板从我脚下滑了出去,在水泥地上留下了一道完全可以气死毕加索的抽象划痕,接着便听到咔嚓一响,那是我的尾椎骨和水泥地亲密接触时的独特声音,然后是我发出的一声惨叫。
“二师兄,你动作真帅。”泼猴全然不顾我的龇牙咧嘴,冲我伸了个大拇指。我试着起身,一阵钻心的疼传遍了全身。“我算明白了革命先烈在白公馆渣滓洞时的伟大了,看来这忍痛可真不是嘴上喊喊就能行的。”我一边用调侃放松着自己的情绪,一边把身上的力量集中在双腿上,试图再次起身。
“不行!”屁股离地也就一厘米,我就支撑不住了,再次坐在地上。“泼猴,来,扶我一下。”我咬着牙,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淌下来。“哇—”泼猴竟然哭了,而且哭的声音无比嘹亮,广场上很多人向他行了注目礼,这小子还挺会抓时机,抹了一把眼泪,冲着一哥们央求道:“叔叔,我老爸残废了,求你帮我把他扶起来吧。”“呸呸呸。”我赶紧驱赶晦气。这泼猴有日子没喊我老爸了,没想到今天在喊我老爸之后,还咒我残废,这点泼猴跟他那已经跟我离婚的妈一个德行,就是不能让我舒舒坦坦地享受为人夫、为人父的乐趣。
在一哥们的帮助下,我总算站起来了,虽然异常疼痛,但总算强忍着走了几步。而泼猴也破涕为笑:“二师兄,你比昨晚电视里演鬼子的那演员演得还像!”
“去去去,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叫王宝强的那演员演的是好人,不是鬼子。”我一边纠正着泼猴的错误,一边招手打了一辆出租车。
“二师兄,我想我妈,她为什么就不能从北京调回来?每个月我才能见她一次,别的小朋友天天都能见妈妈。”钻进车里许久,泼猴忽然一本正经地问我。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我和泼猴的妈离婚已经四个月了,除了执行了法律规定的财产分割之外,我在没有征求泼猴意见的前提下,取得了泼猴的抚养权和监护权。“如果你不让泼猴跟我,我就不跟你离婚,咱们就这么相互折磨,每天争吵,你觉得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好,咱们就这么办。”我是这样要挟前妻许霞的,而许霞也不得不妥协。泼猴是我的命根子,另一方面,如果泼猴跟了许霞,我跟许霞的关系就彻底一刀两断了。出于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我还不想这么快就跟许霞撇清一切关系。
为了不给泼猴的心理造成影响,我跟许霞达成了统一口径:不让泼猴知道我们离婚了,由许霞告诉泼猴,她调到首都工作了,每月十五日左右的那个“大礼拜”才能回来见泼猴一次,而泼猴在这两天,可以在他妈面前任意撒欢。
美女竟然是邻居
“师傅,拐到中心医院里面去吧。”本来想直接回家,但我临时决定,还是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就算不为自己,也为了泼猴,我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泼猴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在医院的骨科,我见到了美女苏麻。我这个人虽然没有被老天赐予特异功能,但是我的听觉却极为发达,以至于即使在嘈杂的环境中,细微的声音都能被我的耳朵清楚地捕捉到。一个死党曾经很恶毒地开玩笑说:“别看你现在耳朵灵光,或许某一天,你眼睛就瞎了,老天爷玩的是‘欲先取之,必先予之’。”
还没走进骨科的门,尽管泼猴蹦蹦跳跳的,分了我的神,我还是清楚地听到一个很柔软的声音在说话:“秦主任,下月开到二百盒,我多返你十个点。”走进去,看到一个身着白大褂的老女人迎面对着我,而她对面,留给我的是一个婀娜的背影,橘黄色的裤子,淡绿色的上衣,整个一棵嫁接成功的小树苗。
“秦主任,麻烦您给看看,我这疼得受不了。”我在为病号准备的凳子上坐了下来,而坚硬的凳子面又刺激了我的尾椎骨一下,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恰巧泼猴这死小子手贱,拧开了墙上的红外线消毒灯,于是听到那美女一声呵斥:“哎,哎,小朋友,别动,别动,那玩意儿漏电。”吓得泼猴赶紧把手藏在了身后。
我抬起头,向美女报以友好的眼神,同时得以细细打量她:二十六七岁的年纪,长发扎成一团,五官算不得精致却耐看,尤其是嘴巴长得很有风采,跟美宝莲唇膏广告上的大嘴那么性感。
我冲她点点头,她笑笑,接着站起身,冲着秦主任说了句“我先走了,电话
联络”。
随后,我就成了砧板上的肉。秦主任让我趴在了一张医用床上,用她那仿佛练过鹰爪功的手在我的尾椎周围来回按压,而从没练过金钟罩铁布衫的我在她的蹂躏下,发出了阵阵呼天抢地的声音,头上冷汗直冒。“轻点,轻点,真疼!”我不住地哀求秦主任,而泼猴直瞪着眼睛,攥着拳头看着我一言不发,让我从心里觉得有了一丝温暖。好儿子看着他老爹受疼,正给我鼓劲呢。“二师兄,你别喊了,你不经常跟我说男人要坚强,就算严刑拷打、手指扎竹签子也要挺住吗?”泼猴的话,让我感觉到秦主任的魔爪仿佛也没那么可怕了,我使劲忍住不发出声音。可这种坚强仅仅持续了不到两秒钟,随着秦主任的一下重手,我腾地一下转过了身子,冲着秦主任一声怒喝:“你杀了我吧!”
秦主任并不理会我的狂躁,慢悠悠地说:“尾椎骨骨折了,本来不用吃药,回家静养就行,你属于耐受能力比较差的,现在我给你开点止疼药。”说完她拿起处方笺开单子。泼猴瞪着两只无知的大眼看着我,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神跟他那跟我离了婚的妈竟然如此相似,眼神中带着重重的不屑。“泼猴,走,回家。”秦主任的话和泼猴的眼神严重刺激了我,我一把抓过泼猴的手,强忍住疼痛,毅然坚定地走出了骨科的门。临出门前我看到秦主任停下手中的笔,把处方扔在了桌子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