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小说还有关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一辈子的恩怨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只有一点,我父亲最后的净身是母亲和我完成的。母亲给父亲擦下身的时候擦得特别的仔细,待她擦完了,母亲又给躺在芦柴席上的父亲穿上了衣服,死去的父亲像是母亲怀里的孩子,任性而自私。母亲费尽了力气,而他丝毫没有任何感谢,跟和生前的脾气一样。
平时要到生产队做工,而做芦柴的时间是利用一天时间的边角边料,母亲就特别盼望下雨,只要下雨,每个人都必须窝在家里,这样流水作业线的人员就齐整了。往往到了下雨这一天,母亲就会很大方地在锅里煮上一大锅面疙瘩,然后像妇女队长一样说,多吃些疙瘩,多吃些疙瘩,上午就开工。母亲负责铡芦花,用小抽钩给芦柴开膛破肚;父亲负责碾;我、素兰和爱兰负责剥柴衣;大姐红兰负责编织。大姐手快,常快得我们五个人都跟不上她的速度,刚见她坐在地上替一张柴席“起头”,一会儿就看见她在替这张柴席“塞边”完工了。如果是晴天,打谷场上的石磙子可以用,我们加把劲,在母亲的怒斥声中跟上红兰的速度是应该没问题的。而到了下雨的时候,开膛破肚过的芦柴要变“熟”,就需要用榔头捶,这是父亲最不愿意做的,但为了儿子的将来,父亲只有用榔头捶下去。一小把一小把,可速度还是慢,往往父亲还没捶熟一把芦柴,没有原料供应的红兰就坐在做了一半的柴席上发呆了。这样,母亲设计好的流水线就断了档,往往这时候,母亲的脾气就上来了,话就说得不好听了。父亲昕了,当然不舒服,手中的榔头落到地上的声音也不一样了,战争的乌云就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上了。不过,很多时候,母亲是忍让的,只要父亲手中的榔头发出异样的声音,母亲就不发脾气了,反而像哄我们一样哄父亲,母亲一软,父亲也就不好发脾气了。做芦柴席的流水线阻塞了一下,又顺畅地流下去了。等到晚上的时候,最早结束工作的母亲就会到厨房炒上一盆蚕豆,然后夺过父亲的榔头,对父亲说,去弄两盅吧。父亲不让,母亲就会喊父亲的名字:周益民。母亲喊到第二遍的时候,父亲就站起来了,慢慢地跑到桌子边“弄”酒去了。
那些下雨的日子里,也有母亲不让父亲的时候。与父亲的慢速度相反,母亲的动作就很快,抽柴抽得飞快,只见她手一拉一拉,一根芦柴就被开膛破肚了。当时我负责把母亲抽好的柴抱到父亲的身边。父亲依旧在不紧不慢地捶,有一下没一下的。母亲看了父亲好几眼了,父亲还是这样,母亲就忍不住了,说,周益民,我跟你换。父亲不吱声,不吱声表示否定。父亲还在有一下没一下的,他只能捶柴,他的手不能剥柴衣,不能抽柴,一剥一抽就会有芦柴刺戳到手中去。母亲越是着急,父亲越是不紧不慢,还放了一个屁。我们还没来得及笑,父亲手中的榔头就飞了起来,落了下去。榔头柄断了,父亲的一屁把榔头打断了,这样的喜剧就是父亲主演的,还经常上演,我们都笑翻了,而父亲一脸的严肃,他是天生的喜剧演员,有时候,很少笑的母亲也会被他逗笑起来。
榔头总是坏,谁也不能怀疑父亲在上面做了手脚,流水线要延续,就得到邻居王四妈家借,我们都抢着去隔壁王四妈家借榔头,但这样的好事往往被母亲指派给爱兰。爱兰很不情愿,有时候借的时间长,有时候借的时间短,不管时间长时间短,母亲都会骂爱兰。爱兰不怕骂,说起刚才去借榔头的种种细节,有些细节明明就是爱兰自己编的,可我们相信,实在太无聊了。就在我们这边闹笑的同时,父亲在那边还在有一下没一下地捶着芦柴,圆滚滚的芦柴在父亲榔头下咯嚓嚓地碎裂着,躲避着。父亲说,这榔头怎么这么生?父亲话没说完,他又放了一个屁,我们没有笑。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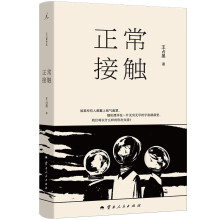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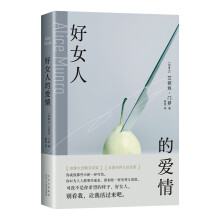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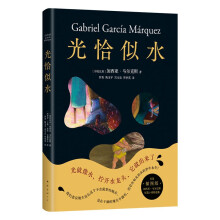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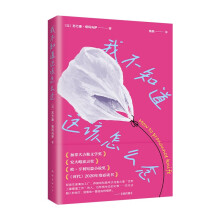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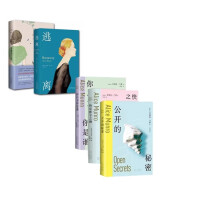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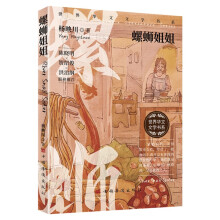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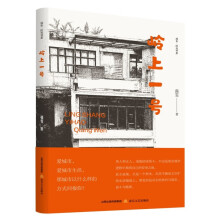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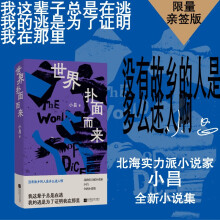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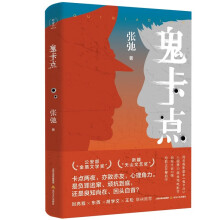
——李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