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晓得作者文心,方才不致对作品曲解、误解。
从谂禅师(赵州禅师)云:有时将丈六金身(佛身)做一支草用,一支草做丈六金身用。
鲁迅先生颇能以一支草做丈六金身用,如《阿Q正传》。《礼记》所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
将丈六金身做一支草用,唯太史公能之。如写《项羽本纪》项羽大破秦军于邯郸一段,不但锋棱俱出,简直风雷俱出,然不见太史公写时之慌乱困难。
不论诸子之说理,屈子之抒情,左氏、司马之记事,皆能以安闲写紧张。虽遇艰难复杂,皆能举重若轻。读时亦不可紧张,忽略古人用心。
文有痛快淋漓、蕴藉缠绵、晦涩艰深之分。
蕴藉不是半吞半吐,不是含糊,不是适可而止,不是想做而不做,也不是做而不肯干。蕴藉是自然。
痛快、晦涩皆是力,一用力放,一用力敛。
《左氏》、《公羊》、《谷梁》皆蕴藉,《世说新语》蕴藉,宋人笔记近之。
汉人文章使“力”。盖汉人注意事功,思想亦基于事实,是“力”的表现。总欲有所作为,向外的多。
魏文帝曹丕不是“力”,而是“韵”。
“力”与“韵”皆非思想。
“韵”盖与“感”有关。“感”有二种:一为感情,心灵的(灵、心);一为感觉,肉体的(肉、物)。
佛说“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属于肉,后一属于灵。“韵”与感觉、感情有关。
李陵《答苏武书》或谓为六朝人伪作,此不可信。即使非李陵,亦必汉人作。文气发煌,绝非魏晋以后人所能有。盖汉人为文,亦好大喜功也。
魏晋文章清新。与其谓为春天雨后草木发生,勿宁谓为北方秋天雨后晴明气象,天朗气清,天高气爽。
六朝文章成熟,尤其在技术方面(修辞)。
李陵《答苏武书》既非魏晋清新,又非六朝成熟,而颇有发煌之气。
美丽、简明,六朝文兼之。简明乃美丽之本。
萧氏父子(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统、简文帝纲、元帝绎)中,昭明太子不及武帝衍,且不及简文帝纲。欲知末路文人情况,可读简文帝传及其文。简文帝没过过一天太平日子。
六朝短赋(小品赋)当以萧氏父子所作为佳。而昭明不及其两位贤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写声、色,真写得好。
六朝时人性命不保,生活困难。文人敏感,于此时读书真是“苦行”,而于“苦行”中能得“法喜”(禅悦)。别人视为苦,而为者自得其乐。
人在安乐中出生,不了解人生;人在苦行中出生,才能真正了解人生。
太平时文章,多叫嚣、夸大;六朝人文章静,一点叫嚣气没有。
六朝人字面华丽、整齐,而要于其中看出他的伤心来。
《世说新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皆可看。《洛阳伽蓝记》漂亮中有沉痛,杨街之写建筑、写佛教,实写亡国之痛,不可只以浮华视之。
若以叫嚣写沉痛感情,必非真伤心。
沈约《宋书》最可代表六朝作风。人皆谓六朝文章浮华,而沈约《宋书》虽不失六朝风格,然无浮华之病。
无论是弄文学还是艺术,皆须从六朝翻一个身,韵才长,格才高。
“气盛言宜”(韩愈《答李翊书》)之文在六朝并不难得。无论何代,只要略有修养。修养,作者皆可做到。六朝长处不在此,当注意其涩。
后人的文章在“结实”方面,往往不及秦、汉、魏、晋。
文章尺幅有千里之势,尤其短篇要如此。公羊、谷梁短,左氏长,而读公羊、谷梁并不觉其短,全在顿挫,个个字锤炼而出。
文章一坑一块不成,成浆糊也不成。首先要清顺,而清顺又要有顿挫。首先要流利,然后始可求顿挫。
六朝文四字一读,改为六字句,便顿挫不足矣。
深刻的思想、锐敏的感觉,二者在文中有一样就有内容。
《左氏传》无中心思想。作史只是要真实生动,不要用自己的意见去征服人,只把事实点出,自然形成别人意见。
文学若从“写”说,只要内容不空虚,不管什么内容都好。如《石头记》,事情平常,而写得好,其中有“味”。《水浒》杀人放火,比《红楼》吃喝玩乐更不足法,不足为训,而《水浒》有时比《红楼》还好。若《红楼》算“能品”,则《水浒》可日“神品”。《红楼》有时太细,乃有中之有,应有尽有;《水浒》用笔简,乃无中之有,余味不尽。《史》《汉》之区别亦在此。《汉书》写得兢兢业业,而《史记》不然,其高处亦在此,看似没写而其中有。
禅宗语录文章美,似《世说新语》。
一丘一壑虽小,伟大或不如泰山恒岳,而明秀过之。
胡适说理文条达畅茂,而抒情、写景不成。归震川文集浮浅,而条达畅茂。条达畅茂之文是富于音乐性的,而易成为滥调。
明末黄梨洲、顾亭林真了不得,能知能行。黄梨洲的《原君》《原臣》,在专制时代能有此思想,真不易。
《阅微草堂笔记》,腐。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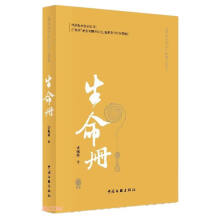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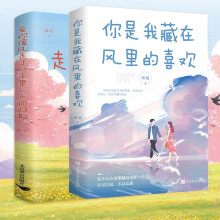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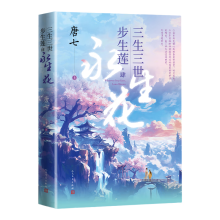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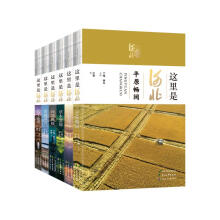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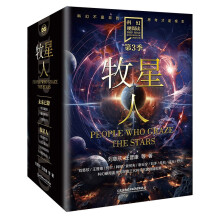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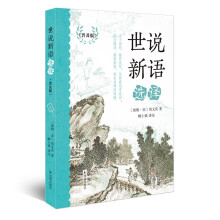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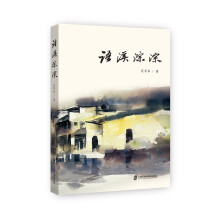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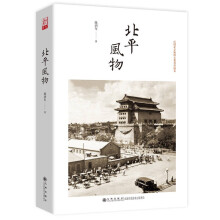
★先生的才学和兴趣,方面甚甚广,无论是诗、词、曲、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甚至佛教、禅学,都曾留下了值得人们重视的著作,足供后人之研读景仰。我以为先生平生较大之成就,实在还不在其各方面之著述,而更在其对古典诗词之教学讲授。因为先生在其他方面之成就,往往尚有踪迹及规范的限制,而唯有先生之讲课则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词能得其神髓,而且也富于启发性的……凡是上过先生课的同学都会记得,每次先生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直接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然后才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我聆听顾随先生讲授古典诗词,前后曾有将近六年之久,我得知于先生的教导、启发和勉励,都是述说不尽的。关于先生讲课之详细内容,我多年来保存有笔记多册,现已请先生
——国学大家、加拿大哥伦比亚不列颠大学教授叶嘉莹
★顾随多才多艺,写诗、填词、作曲,都创有新的境界;小说、信札;也独有风格;教学、研究、书法,无一不取得优越的成就。
——诗人、学者、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至
★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一位极为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
——红学家、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周汝昌
★顾随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笔下真是神乎技矣。
——国学大师、作家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