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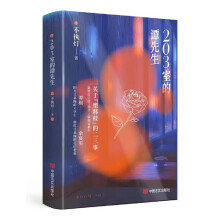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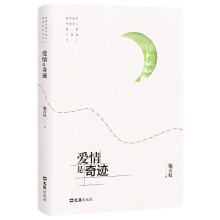

地安门大楼是个大屋顶的筒子楼。这里住的孩子只要年龄相仿,基本上都是同学。学校就是楼后胡同里的黄化门小学。这些胡同里的老住户大部分都是旗人,祖上都吃过“铁杆庄稼”,就是不当差不干活也拿钱的主儿,人称八旗子弟。
这些人家普遍规矩大,讲究多,而且还有许多能迷死小孩子的玩意儿。我的花鸟鱼虫启蒙全是在这里拜的师傅,雪坎这辈子养花、喝茶的毛病也是打小在这里沾的腥。
记得那时下课铃一响,我和雪坎就开始疯抢作业,争取十分钟搞定,然后跟酸梨、马四去他们院弹球,拍三角,可奇怪的是这二位游仙从来不做作业。我说:“你们就按我的作业本划拉几笔抄上不就完了,何必明天老师检查作业,又不踏实。”
“我没不踏实,抄作业我才不踏实呢,万一再抄错了,你说冤不冤?” 酸梨摇头晃脑地说。
“你他妈就不怕老师找家长?”
“不怕,你问四儿啊!我从来不怕这个。”
“真的,我也不怕。我妈都听我的。”马四在一边证明。
“那为什么呀?” 雪坎也不信。
“不为什么,我俩都是亲妈,而且都是护犊子的老娘在家打旗⋯⋯”
“我靠,谁也不是后娘养的。” 雪坎不服气。
“行了,行了,这咱还真别不服气。咱的娘,别人找上门,准是先骂儿子,后赔不是,凡事都是自己孩子的错。”
“还玩不玩了?要不玩我们俩先走了啊!” 酸梨背起书包拉着马四要走。
“别他妈拿糖①了,我今儿就上你们家玩去,我还要给你妈告状哪!”我和雪坎跟这俩小兔崽子一溜烟跑出校门,直奔腊库胡同。十分钟的路,因为腿急,五分钟就跑到了。还有比我们更急的,王南和易明已开始在门洞里扇洋画了。见我们来,他们收起烟盒,准备继续昨天的弹球大战。
我们俩人一组,玩出锅比赛,赢了的下去,输了的留战,给个捞的机会。玩了四轮,门口进来了一个身材微胖、皮肤白皙的中年妇女,手上网兜里拎着西红柿、黄瓜之类的蔬菜,不用说,我就知道酸梨这皮肤漂白、大腮帮子随谁了。
“行了,散了吧,该回家吃饭了。别忘了洗手啊!”梨妈一下命令,王南、马四、易明撒丫子就溜了。我和雪坎像二傻一样站在当院,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二林子,这俩小孩是谁呀?”他妈是不会叫他酸梨的,而我们现如今都想不起他还有个孙林的大号。
“这是陈星和雪坎,也是我们同学,都住地安门大楼。”
“新来的?也都听二林子念叨过,洗洗手,进屋待会儿吧。”
我和雪坎洗了手,屁颠屁颠地进了屋,为了表示礼貌,我和雪坎老老实实地站在门边,我说:“阿姨,我们俩⋯⋯”
没想到这半句话忽然让梨妈翻脸了:“谁是你们阿姨呀?你们俩怎么着嘛,我知道你们大楼里管保姆都叫阿姨,我又不是你们老妈子⋯⋯”
雪坎被训蒙了,也横着出来一句:“那跟您叫什么呀?总不能管您叫祖宗吧?”
梨妈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谲的笑容,说:“这孩子,不吃卦,还当真了。阿姨逗你玩哪,别往心里去。”
“我们不想跟您叫阿姨,我们想和二林子一样管您叫妈⋯⋯”我说。
“哟,这孩子没发烧吧?”说着她伸手摸了摸我额头。
“我没烧糊涂,我是真心说的梦里话,我和雪坎都想认您当亲妈,您收不收吧?”
“嘿!这孩子半真半假还真把我闹迷糊了。你爸是曲艺团的吧?”
“不是。”
“可我是啊!戏词里没这出啊!进门就认妈,连点拐弯话都没有,难道你们俩是我上辈子走丢了的黑白小兔儿,如今回窝来了?”
我们都没憋住笑,气氛一下亲近许多。雪坎捅了酸梨一下:“你妈可真逗。”
“我妈是曲艺团唱大鼓的,左邻右舍都知道当年我妈是国宝。”
“国宝?”
“那都是早年间的事了。不提它了。”梨妈笑起来可真好看。
“不行,不行,后进门的孩子也得知道干妈的身世。”
“这小秃子还挺霸道,好,告诉你,我叫彩云仙,四岁时师傅就托着我登台演戏,九岁时红遍大江南北,在上海大舞台演出时场场爆棚、炸窝,观众都冲到台口伸着手嗷嗷叫,返场十七次都不让下去,要不是台上悬着‘许看,许听,不许摸’,还有我师傅带着一帮武行守着台口,观众都敢上台⋯⋯”
“干妈,您可真了不起。”
“人这一生都有闪亮的时候,那时候北平城里不知道毛主席的多,不知道我彩云仙的少—我说的可是新中国成立前,不信回家问问你爸你妈去。”
“妈,你说话又走板了啊,我爸不是不让您提新中国成立前吗。”
“还不是因为你拐了这俩孩子上家来认妈了?说说,为什么?”
“陈星说就喜欢有个护犊子的老娘儿们当妈,雪坎也起哄非来看您,所以就来了。”
“小子,二林子兄弟姐妹五个哪,你知道吗?”梨妈指着我。
“知道,从此他们也是我的兄弟姐妹。”
“话是受听,可我彩云仙没这个造化,收不了你们俩了。”
“为什么?干妈都叫了,您又变卦了?”
“我是护犊子的老娘儿们不假!而且心比天大,恨不能天下所有的孩儿都是我的儿女,可我养不起。”
“我们不用您养活。”
“敢收就得养,收养,收养,哪有光收不养的?”
“我们真的不用您养,将来我们一定养您,您就认了吧!”
“还真没见过这么缺爱的孩子,可认干妈也不是件说笑话的事,你们俩真的不是胡来吗?”
“不是!我们是真的愿意,我们会比二林子更孝顺您。”
“行了,你们俩孩子我收了。一会儿把名字和家庭住址写月份牌上。我还有一个条件⋯⋯”
“您说,是不是我们该给您磕响头?”
“干妈没有那么旧,我问你们一句,这件事你们打算和你们的亲爹亲妈说吗?”
“不打算。”我坚决地说。
“我也不想告诉他们。” 雪坎也附和。
“那我就放心了。这是咱娘几个的秘密,除非天塌了,否则我不会见你们爹妈。”
“知道了。”
“小林子,赶紧趁天擦黑前上东板桥副食店买两毛钱肉馅、一毛钱黄酱、五分钱茶叶末⋯⋯”
“干妈,我们俩就不在这儿吃饭了,食堂还有饭。”
“废话,不许不懂规矩,今儿是来不及了,给你们擀点儿面条吃,等将来你干妈做七层肉饼、三鲜饺子,保证你们吃得走不动道儿。”
“我现在就走不动道儿了。”
“去吧,和林子一块儿打黄酱去吧。”
“得嘞!”我们哥几个一溜烟冲出了孙家的小院。
这孙家小院在东板桥腊库一带虽不显山不露水,却是收拾得方方正正,干干净净。花鸟鱼虫、大枣树、三间正房、两间厢房,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四合小院。据说是新中国成立前,梨妈要立身北京发展,师傅给精心挑的,说这里是皇城脚下,风水好。梨妈是天津人,天津卫起家,北京城里安家。这个独门小院,对外可不独,胡同里的孩子,只要认得酸梨,没有过节儿,敞开来玩,要不是酸梨五年级才转到我们班,我早来这小院儿了。我和这小子认识才半年,也没细攀过道,现如今才知道,孙爸爸以前也在曲艺团待过,是个万金油,吹拉弹唱无所不精,也编过本子,拉过大幕,强项是吃开口饭,评书、相声、快板,说来就来,京津两地耍口条牛×的角儿,提起“云里飞”(孙爸的艺名),没有不高看一眼的。但云师傅在团里不合槽,嫌不自由,老有人拿他说事,与其见天和人干仗,不如辞职单干,这样梨妈也省心,领导也清心。他就在鼓楼后开了个书场,每天午后三点开始,两段书,场场满客,见天儿“捡钱”,听书的都是老人儿,熟门熟脸,有俩闲钱,这是他们解闷喝茶的地方。云师傅还有个搭档,叫金大喇叭,高门亮嗓,零碎多,喜欢说野活,据说祖上也是位贝勒爷,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赵连龙大战北京侦缉总队》里的赵连龙:“他一身短打扮,一双快靴,一脸大煤渣子,走起夜行步来是膝盖打胸脯,脚尖打屁股蛋,一溜儿滚翻而去,那是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骓。知道嘛叫骓吗?千里马,万里驹,滚风骓。最快的就是这滚风骓,眨眼都赶不上它,一溜烟就没影了。”
当然,泡茶馆听书这都是后话。咱再说回眼巴前儿。那天晚上我们买完东西回来,正赶上干妈在小厨房里擀面条,昏暗的灯光下,她穿了个开胸小褂,两个奶子像两门炮似的上下颤动着,真好看。我都看晕了,心里一阵狂跳。不知是这狂跳的动静暴露了我在门外黑影里的位置,还是她早就发现了我⋯⋯反正她连眼皮都没抬:“瞎看什么?当心看在眼里扒拉不出来。”
我觉得血噌地涌上来,脖梗子都烧红了,上个学期刚矫正过来的结巴又犯了:“我没⋯⋯没瞎看,真的⋯⋯真的⋯⋯”
“别不说实话,干妈又没怪你,男孩子早晚要开眼的,只是等你到了往外掏坏的年纪,干妈早就不在人世了。”
“ 我不会往外掏坏的,我就是想,以后谁敢欺负干妈,我就弄死他!”
“哟,这孩子还是个狠角儿,看来我这后半辈子要指上这个窝里横的秃小子啦?”
“我不是‘窝里横’,干妈要有事,我真敢拼命!”
“唉,别说那没用的了,虽然干妈年轻时就喜欢你这种一不要脸二不要命的狠角儿,可我不希望你以后闹事,折我的寿。”
“我没不要脸,也不会给你惹事。”
“行了,别跟我犯轴,往深了说,你也不懂。你们现在还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年纪,回屋和他们玩去吧,我这儿一会儿就好了。”
“雪坎和林子玩跳棋呢,我本来是想过来帮你干点儿活。”
“干活用不着你,不愿走,陪干妈说会儿话吧。进来坐,炉子边有个小板凳,嫌热就贴墙边坐。”
“干妈,您不说有五个孩子吗,为什么身边只有二林子一个人?”我进了屋。
“简单直说吧,你干爹老根儿是通州府人,老家有老宅,有人手,婆家心疼我和云师傅—你干爹,知道我们又要练功,又要演出,所以把大闺女、大儿子和小三儿都接乡下去了,那地方宽敞,伙食也好,到礼拜,他们就回来了。所以平时家里只有二林子和小红。”
“那怎么没见小红啊?”
“她才两岁,就在腊库幼儿园全托,要不是易明他妈当园长,还进不去呢。”
“那干爹也是唱戏的吗?”
“你说云师傅?他什么都会。当年在天津他也红过,会的玩意儿多,得罪人也多,如今落了魄了,在鼓楼后说书呢。”
“怎么没见他在家?”
“白天他见天儿在家,您上学,我上班,照不上面是因为他有夜场活,回来得晚⋯⋯小少爷,我家底儿都撂给您了,咱也该开饭了吧?”
“是,我去摆碗。”
那天晚上,我和雪坎甩开腮帮子猛吃,把给云师傅留的份儿都给招呼了。干妈笑着说我们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是我第一次吃老孙家面条,面条筋道滑润,小碗干炸的黄酱又香又咸,菜码是青蒜、青豆、青辣椒丝,外带一盘切成片的大白蒜。用干妈的话说:“百姓解馋,一辣二咸,这种饭痛快。”
就在我和雪坎吃撑了撂筷子的时候,干妈变戏法似的拿出几个小酒盅,一盘铁蚕豆,一小壶烧酒,然后问我们:“小哥俩以前沾过酒吗?” 见我俩摇头,又说,“那就对了。今天不管真假,以后星星和雪儿见我得叫妈。”看我俩拼命点头,干妈脸上放光了,“所以这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要给小哥俩开开蒙。”她随手给酒盅里斟上了酒。
“酒这东西是男人的回味药,你们就一口闷下去,这火辣辣的感觉会让你们记住。做人有时要有这种感觉的。没事,你们肚子里都有食,来吧。”
酸梨是个小酒虫,打小他爹就用筷子头蘸酒喂过他,所以他没事人似的一仰头干了,随手抓了一把豆吃起来。我和雪坎因为做足了喝敌敌畏的感觉,跟着干妈一口闷下去以后居然也面不改色。后来听酸梨说,这是他爹早年淘换来的六七十度的烧刀子酒,平时都打零酒舍不得喝。“今儿我妈是真高兴才起心祸害了我爸这点宝贝。”
这酒的威力开始显现了。它一路烧着,从喉管冲进胃里,渗进血里,人开始红了,有点儿要沸腾了,只是被烧的喉头还让你一时说不出话来。干妈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把事先闷好的茉莉高碎①挪过来,给我们一人倒了一小碗:“怎么样?喝点茶吧。”
我抿了一口茶:“真棒!干妈,这酒真棒!”
“真棒就好,这东西以后不许沾了。等你们成人以后再开戒也不晚。能听干妈的话吗?”
“是。”我看着她,感觉到世上的亲人真的是需要自己寻找的。
温馨提示:请使用太仓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