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他俩坐到了四趟车,最后才搭上一辆手扶拖拉机般的三脚猫开往海角渔村。
可乐从来没有在悬崖峭壁上俯瞰过龟缩山脚下的大海。山岩好像是阵地,而大海每天都会发起一次以上的总攻,不因为对方居高临下而放弃。海风空旷地吹。大海现在不是高山仰止,而是尽收眼底,俯拾皆是浪花。鸟瞰令人自觉渺小,随时羽化无形。人的目光愈拉愈长,变成了鹫鹰坚毅的视野,苍茫、雄壮、悲愤、奋起。天、地、海和人,随着视野而躁动不安。而简陋的三脚猫好像在机耕路上不断晃悠震动,就像给人的想象插上了翅膀,会幻想现在冲天而起,拍打着双翅翱翔。阳光明媚,海水碧蓝,波光粼粼,氤氲叆叇,仿佛海面有多大,铺在海面上的渔网就有多宽。海水就像盛在一个天大的器皿里,海水不安,海水激荡,海水满溢,海水要飞扬,海水要破坏。眼底再远处,是一大片快要被海水湮没的红树林,它们却镇定自若期待每天的没顶之乐,它们手拉手连成天边海底的一片深绿色,与蔚蓝的大海、洁白的沙滩融洽成万里无云天空下的三原色,感天动地的“三足鼎立”,毫无演义,而是涨落日常生活的伟大真谛。此刻,热气腾腾的三脚猫噗噗噗嘶呜地使劲爬山,愤怒地绕着山梁突突攀登,拱上天际。而在山的阴面,看不见了大海,山窝里是茂盛的树林和一小畦一小畦的旱地,间或一眼破败的泥坯屋,相伴同样孤零零的坟墓,诉说着前世今生的片断。海边的群山丘陵没有高耸入云,也没有云遮雾罩,一切都是那么葳蕤勃然而明朗开阔,阳光蒸化,海风涤荡,远处山叠山,山外有山,一山还比一山高。但不久三脚猫又绕回大海这一面,像一只小松鼠,上蹿下跳,变得充满灵气和顽皮淘气,显露可爱一面。可乐从来没有想到距离城市繁华一百多公里,还有着这样一个可口生活过二十几年的天之涯地之角。
人与人的相识,差不多就是山和水的相逢。
海风把可乐的一头金发,像碧波一般犁向脑后。他像一次远足郊游,他要放飞困顿的自己。
三脚猫在村头一座小石桥下急促地喘了几大口气,犹如山区里的一只褐色猪屎虫,终于停止了疲于奔命的趵突,车头马达那儿,鼻孔般地飘浮出一缕接一缕水烟,柴油味呛开来,细心听,还会响起咕隆咕隆的水声,似乎发自腔腹,回流心脏。世界一下子显得十分平稳和安静,耳朵疲软地耷拉下来,五脏六腑也归位。小石桥是用巨大的麻石条铺的,一条嘻嘻哗哗的小溪从桥下一个桥拱笑过,然后闪了几闪细腰就不知深浅一步一个脚印出海去了。桥下的鹅卵石染着青草颜色,顺水漂流着几片烂菜叶和一根根枯槁的稻梗,小溪两旁是一蓬蓬生机勃勃的蒿草,草丛中斜搁几张散了一半的竹筏,满是苔藓的竹筏已经腐朽散架。
桥头两溜卖菜摊贩中,挤有一间理发店,店外头顶支着一方撕开的残旧白布标语,歪歪斜斜地蔽遮下午的似火骄阳,从残破的大字上看得出是一种全国青少年都要喝的补血剂。一个干瘦老头怀抱一块疙瘩初成规模的木头在削什么乐器。可乐穿插过去,可口拽住可乐,说怎么,真在乎一头金发?
可乐说入乡随俗。
可口说你不是喜欢不俗?
那是大俗。
那你就剃光头,还俗是了。
来这儿出家倒很妙。
有女神送你出家,你能静心养性?可口拉可乐走,说算了,反正我跟我家里说了,我带回一头金毛狮王。
金毛狮王乖巧地跟可口走到海堤边,她的家在渔村最西头,跟大海面对面,中间隔着沙滩上的一溜马尾松林,像吊挂着墨绿色的窗帘。马尾松那一扎扎的松毛酷似马尾,仿佛在马厩时温顺垂落,大风起兮奋蹄嘶鸣,马尾高耸抛动,像一群水墨中的冲冠怒发奔马。马尾松树干笔直高大,青黛色的树皮粗糙虬结,屹立大海边既像少女的一头温柔披肩长发,也露出男子汉的孔武遒劲。可乐和可口踏着马尾松落下的松软松针,脚下有点滑溜,一棵棵马尾松的苍劲根部裸露了一半,它们像老人胳臂,紧紧拥抱养育自己的海边沙滩,这片腥咸土地,带着光阴鳞片,让岁月迎着太阳闪闪发光。一旁是相隔不远的平房,用碎石花夯实筑成,围起一个小园子,支一张篾席,晒着一些开了肚的门鳝、油鳝、滑鱼、剥皮鱼、银尾鱼和杂鱼。满海滩的碎石花向海缓步倾斜,几乎堆积上堤岸,石花像断掉的一根根小手指,是无数珊瑚虫临死的剥落,花儿一般完成凋谢,身上的小针孔是珊瑚虫的气泡吧,从海底冒上岸来,完满了一个轮回,还嘟着小嘴可爱而终。坎坷不平的堤坝也是用石花夯实围砌,但抵抗住了海潮无数的冲刷拍击和拉拢腐蚀,跌跌宕宕顽强向前延伸自然意志。渔村后面就是青翠山岭,山下是小溪滋润的稻田。涛声寂静,飞鸟远遁,隐匿在这个山岬角上的半岛,被世人遗忘,也遗忘了世人。这就是古人说的物我两忘吧,尽管对于可乐而言,他一向物我两全,自以为是多过自以为非,像他这种公子从来没有忘过什么,也没有缺少过什么,正因为如此,来到渔村,他有点惶恐的自责,像来到教堂跟前,不禁为自己奢侈和没有忏悔的过往惭愧起来。
可乐走到马尾松树下,抓起脚下的一把黄稔的松针,对可口说,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可口扭过头来说,是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落后的地方吧?
可乐自嘲地笑笑,说我真的像落难公子?
可口往前走去,大声说,这要看你本来是不是将自己当作公子哥们。
可乐将马尾松松针一节节拔出来,随它们从指缝间洒回沙砾地上。
加快步伐的可口停在一个小院子前,她抬高一扇齐腰高的竹门,闪身进去,回头让可乐小心一点。可乐随后也闪身进去,原来门前的空地上还圈养着一窝毛茸茸的雏鸡,大母鸡浑身鸡毛暴发,像刺猬般怒视来者,嘴里发出不间断的咕咕咕警告声。可口清脆地喊一声妈!我回来啦!
一位身体微胖面色黝黑的四十多岁阿姨从房子里颠着双脚应声走出来,带出来一身人间烟火味,她粗糙的双手在围巾上一下又一下揩着。可口望着可乐,说妈,这是可乐。
可乐忙躬了躬身子说阿姨,给你添麻烦了。
大老远来,说这些做什么?可口的妈和善地看了一眼可乐,很热情地说中午你姑姑就打电话来村头小卖店,说你今天回家来……风风火火的,也不知你赶什么圩。我早上凿了些牡蛎,先喝碗汤。
可口叫可乐提行李进屋,说妈,爸出海啦?
一早出海啦。
回来一定有花蟹。
你爸哪知道你今天回来。可口的妈说着走回厨房,说正炸鱼饼。
可口让可乐将行李放在屋子北面的一间小房间里,说你就睡那儿。这是可口弟弟的房间,可口弟弟和妹妹上镇里中学了,周日才回。可口从一架木梯上爬上屋子深处的一层小阁楼,说可乐,你从下面递我行李上来。
可乐托着可口的行李,连带自己也一块递上去小阁楼。这是用船板搭起的小阁楼,漆着淡淡的桐油,垂落收拢的蚊帐,一排书就倚在阁楼的墙边,像一个小船舱。可口说你先别上来,我得扫扫灰尘。
可乐脱了鞋,像狗一样趴在阁楼木板上,体验着温馨的黑暗,用想象的触须上下抚摸,四处嗅着可口的味道。她跪着前行,推开一扇小窗,光线骤然像投影灯一样罩在她身上,她说从这儿可以看见大海。可乐却没有睁开眼,他说我想听海,便从身后贴近可口,她坐下来让可乐像堤坝一样围起来。他们沉默地吻了,嘴唇试探着接触,像蜻蜓点水,然后吸得长起来,深起来,但尽量不要发出吮吸声。海水和沙滩永远相吻。
他俩依依不舍地松开后,睁开双眼,从小窗口打望大海,像一帧底色明亮的油画,海浪前涌后仰,多像画笔在大胆地着色。只有在大海面前,他们才变成一帧涂上自己色彩的油画。
可口的妈在厨房叫可口下来喝汤。他们才一前一后下来。这个小阁楼是一个隐秘的地方,最适宜做闺房,既是实在的栖身之穴,也是少女想象中的空中楼阁,或者是少女的船舱,从这儿渡向花季和雨季,一直到花谢了,雨停了的城市泊岸。可乐下梯子时对可口说,在这儿幽会很酷噢。
可口推了推梯子吓可乐,说你说我偷汉子?
还差几级着地,可乐就跳下去了,说要偷就偷我。
可口啐了他一口,说你以为这是你们的酒吧?
可乐边穿鞋边抬高头说这是你地盘,我的海市蜃楼。
可口哼着鼻子,趿起拖鞋走去厨房。
喝着清甜的牡蛎汤,可乐对着可口笑,可口问笑什么,没喝过?
可乐啧啧地说有靓汤喝,我就偷笑。
可口的妈从厨房出来,笑眯眯地说,你来这儿,别的不敢说,这种汤每天管你喝得肚圆圆。
可口搁下碗,说妈,你这么好招待他干吗嘛?让他自己去凿牡蛎挖车螺好了。
可口的妈嗔怪地乜了女儿一眼。
可乐说阿姨呀,可口说得对,我正想自己动手养活自己。
可口的妈愣了一下,说你叫我家的乐艺什么来着?
可口忙抢过来说妈,说来话长,你不懂,我还叫乐艺,但也叫可口,我们是在电脑上玩耍叫起的。
可口的妈很开通,说我以为你改名换姓了。
可口抱着她妈的肩膀,撒娇着说哪敢呀!我们是觉得好玩才叫的。
可乐要去卫生间。可口嚼着碗底的姜丝,哼了声,说没有,只有茅厕。
可乐佯装很急了,弯下腰来说就茅厕……
可口带可乐去屋后的两块半人高的石壁露天处,说就这儿。
可乐说奔流到海?
是不是要我示范一次?可口笑着捅了捅可乐的小肚子,三跳两跳蹦开了。
回到饭桌上,可口的妈悄声对可口说,听你姑姑说,他是大官人家公子,你们是不是好上了?
现在还好。
不要像换名字玩耍啊。
可口笑笑。
可乐从屋后回来,说我想下海泡泡。
可口的妈不由分说地摇摇头,慈祥地说现在太阳太大,等太阳下山再下水。
可乐说可口你陪我泡?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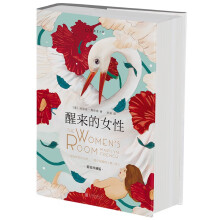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