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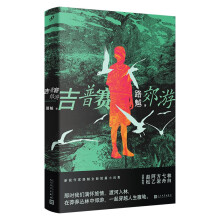







小说写了中国历史上得到正史《史记》记载的一段“大历史大传奇”:秦始皇为了长*
不*,派遣齐国方士徐福到东部大海寻找“三仙山”和长*不*药,徐福趁机率领三千童
男童女和五谷百工,东渡瀛洲,一去不归,建立起新的王国的故事。
小说将徐福不凡的一生――齐国都城临淄求学、卧薪尝胆、催人泪下的爱情、密谋
起事、远渡重洋、晚年婚事与立国……一一展现出来。*后,即将被拥立为国王的徐福
面临一生*痛苦的选择:老之将至却要迎娶土著新娘、在*为厌弃王位的时刻,却要被
迫戴上皇冠……
瀛洲思絮录
齐人徐巿(巿,也作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巿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徐乡城,汉县,盖以徐巿求仙为名。
《齐乘·古迹卷》
第一章
……
在漫长无边的徘徊中,在经年累月的沉湎中,人会认梦成真,呓语不息,以至于手记自诵。分不清是我还是徐巿,乘楼船登瀛洲,宽袍广袖。从此一别卞姜(注:卞姜,齐人徐巿的妻子,东莱人),挥泪而去。
徐巿(福)为秦王采长生不老药一去不归,携走三千童男童女。斯人离去三千年,历史传奇或已渗入几代人的血脉。我们已渐渐不再满足于此岸的遥想,于是转而倾听彼岸的诉说。
……我一度非常谦卑,以便遮掩内在的顽皮和狂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的底细、我内心的隐秘与曲折。我常常在深夜、在一人独守时让思绪任意飞翔,放纵心猿于九霄。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开始学会了息声敛口,极少诉说和相告,哪怕是对挚友、对爱妻——我与她已不能分离。我对其何等疼怜。多少年了,她因我而历尽坎坷,我们真是相濡以沫。她总是无望地期待,直到最后。万般愁绪都连着一个“走”字一个“逃”字。无言的长夜,卞姜吻我不止。
她原是商人之女。黄县这个地方出了不少巨贾,贩桑麻、粳米、丝绸,去临淄、泰南,西走鲁国、远涉长安。她的家世颇有来历,算来还是滑稽多趣、大名鼎鼎的淳于髡的表侄女。
我们都深藏了一句话,都知道秦吏不会让我们同登楼船——随着那个时刻的挨近,夫妻二人都缄口不言。午夜青杨细语,南风徐徐,此岸在赠予我们最后的温情。
后来一切果然不出所料……
儿女情长,英雄气亦长。几年光阴转瞬即逝,我成了一个小心翼翼、四十岁两鬓皆白的俊男。我离开了她,我们从此永远只能隔海相望。我的故事太多了,如今都留在了那个海角、那片大陆。我也远离了对手。遥望彼岸,此时依稀可见阿房宫里烛光辉煌。这让人衰老的光,这让人迷恋的光。而今我足踏凄凉蛮地,正可以像春生野草一样茂长。
当年,我在百无聊赖、无计可施、等待和观测之时,几近绝望。经验和苍老的皱褶都掺在其中了。人在疲备中成熟。懒得行动中的行动往往也可举大事。
我三十八岁那年的一个黄昏,发现持简之手颤抖不已,视物昏花。一阵惊惧之余,心生万分急切。它催人奋力,又加剧人之萎颓。我常常也只有让顽皮的畅想来稍稍滋润,等待来年如期萌发之青杨。
长期以来,海角上只有少许人知我酒量,也知我身世来由。他们都是守秘的命友。如若不是一介草莽,那么放怀狂饮者可能正预示了他的顽皮。而在秦王的那班臣僚眼里,世上的顽皮者或可不必提防。这自然是个小小诡计。
能够一走了之的人,都是旷百世而一遇的妄徒、圣人、色鬼、术士,是从不兑现的大预言家,或者是个酿私酒的人。我后来被看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我最好沉默。
那是一场庄严的赌。本钱很大,押上了身家性命。我一直悄悄埋藏着使命,后世人却要一再地发掘,并将其放在阳光下照晒。可是他们不会知道这使命的青苗萌发在什么根须上。他们怎么也弄不懂,因为终究与我隔开了十八重的冥界。我很爱后来人,爱他们的鲜嫩如花。但爱又极易埋没理性,我镇定下来时,却不由得生出阵阵悲凉。
他们往我身上涂抹难闻的垢物,比如把我说成一个绝望而无义的骗子,尽管并没有多少依据。这种涂抹与我当年做过的事情性质相似,所以说等于应了“吾之初衷”。可怕的倒是另一些人的相反的举止。
那些人是些虚荣的地方主义者,所以又会施予我双重或多重的误解。古怪的推测,小肚鸡肠的盘算;连船队航行之迹都茫然无知,更遑论其他。他们的虚情假义于事无补。地方主义者从来睥睨精神,却又企图依此挽救萎缩的经济,甚至公开无耻地宣称要以之骗取物利。
他们奉我为“伟大的航海家”。“伟大”倒谈不上,因为东渡瀛洲者我既非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那些黄县沿海和周遭岛上渔人,不止一次在风暴中抵达这片无名的荒凉。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将这片荒凉派上了更好的用场。对于一个人而言,关键是要有超凡脱俗的眼光,那一瞥之间的识别、鉴定,以及心中生出的奇思妙想,往往是凡夫俗子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
我说过自己曾经狂妄而又顽皮。有人会直盯盯地看着我两鬓的白发,怀疑这种“夫子自道”。其实他们不懂。智者就在游戏中衰老。有时游戏也很麻烦。
嬴政王可视为我的游戏伙伴,而非雠仇。我当年甚至多少喜欢上了这个目如鹰隼、鼻如悬胆的西部人。他的衮袍与冕旒都遮不去那一身顽皮相。有游戏能力的人即便尊为帝王,也未能免除这一特征。嬴政当年长我许多,一举一动颇为敦厚,步履迟缓。他像一切热衷于游戏之道的人一样,乐于忽发奇想,筑长城建阿房,拜月主求仙药,愈到老年愈是迷恋起这些玩艺儿。
作为东莱故国的贵族后裔,我的仇雠是齐,而非秦。秦为齐之仇雠。这之间的交织参错真是奇妙。齐灭莱夷,而秦灭六国。齐是莱夷人的直接毁灭者。虽然齐人后来乐于说齐莱一度交好,化莱为齐;但实际上那是齐人灭莱,空取渔盐之利。齐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齐国很快重蹈莱夷的复辙。这即便不是通常莱夷人所说的“报应”,也算是命数。
国与人的命数一样,神渺变幻不可推测。
我自有一个预感,它关乎秦王嬴政:这个“千古一帝”身后也隐隐追踪着一只小小的“黄雀”,这恰是他始料未及的。他已疲惫,而那只千娇百媚的“黄雀”正当青春,在三月天里翻飞嬉戏,以逸代劳。我预感到他也“快了”。
谁身后没有一只小小的“黄雀”呢?
午夜走上甲板,从海湾里望去,到处是密挤的楼船。这在荒凉之地的土著看来,无异于一场梦魇。飘忽游移的灯火与水波互映,流动闪烁,神妙难喻,在我看来也是五千年未曾经历的奇观。
这正是我的一个首创,一次得意的杰作。从闪亮的船灯上判断,赖在船上者大有人在——我已三番五次令全部人马分营逐日登岸,一月内筑屋垒城,安营扎寨,船上只留少许守备……看来经常返回楼船的不仅是“童男童女”,还有弓弩手和方士。他们像我一样,需要经常嗅一嗅船上的气味。舱里满载了莱夷的气息,彼岸的烟薰。
我曾把他们频频返回船上视为怯懦。因为土著时常劫营,较之岸上新营,船上毕竟安全多了。现在看是我在妄断:能随我穿越茫茫浪涌叠嶂、穷十万水路者,哪有这么多怯弱之辈!
像我一样,他们这是最后的徘徊。……看着这片摇荡的船灯,我心中渐渐生出一个残酷的决定。
瀛洲思絮录
附:
忧愤的归途
温馨提示:请使用太仓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张炜是一位充满深情和深挚的忧患感的书写者,始终以理想主义的诗情而高歌低咏。——王蒙
张炜是中国当代*富创造力和用心灵写作的作家之一。他是纯文学园地上执著的坚守者;是一位充满深情和深挚的忧患感的书写者;他始终以理想主义的诗情而高歌低咏。
他追求着与辛劳着。他继承了经典大家的笔耕精神,他是中华当代文学园里的辛苦的园丁。他的作品总是有着一股导人向善的力量和一贯的道德激情,直指灵魂和生命。
――王蒙(著名作家)
在30余年文学创作的历程中,张炜对文学始终葆有一颗赤诚之心、虔敬之心,孜孜不倦地大量读书,潜心有难度的写作,有时不惜将自己逼入困境,在创造之路上不断地攀登与**。我相信,没有不存在困境的作家,没有困境,便无所谓攀登与**。
――铁凝(中国作协主席)《张炜和他的小说》
张炜身上*文学的东西,就是诗意,他也是一个抒情诗人。我特别喜欢他的小说。他是我认为的正面的作家,有美好的情感。“美好的情感”这个话现在已经被批判得没什么价值了,可事实上作品的好和坏一定是这上面来见分晓的。
――王安忆(著名作家、上海作协主席)
中国很多作家是学会了在浑浊的世界里面看问题。张炜却始终是一个例外,他是在这个浑浊世界上面升到一个清流世界,这个世界,我认为是张炜独创的,他是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文学经典中走向高尚境界这一路的血脉。
——陈思和(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评〈你在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