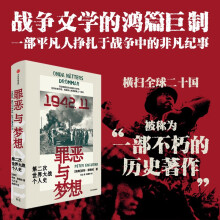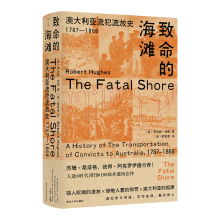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在这个庞大的历史复合体中,西欧扮演了一个边缘的角色,在进人中世纪很长时间后都非常落后。迦太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是了不起的民族,但是他们对于从地中海东部传来的文明模式并未做根本性的改进。罗马人同样如此。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控制了希腊化的东地中海地区,在其西北部边缘地区建立起城市,但是他们自己却总是从东方寻找文化上的指导。甚至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他们所创造的罗马法,也毋宁说是地中海地区的创造而不是意大利的创造,虽然在长时间里它是用拉丁语表述的。直到中世纪盛期,西欧人才开始真正达到文明核心区的创造力水平。十字军东征之初,无论是与希腊人还是阿拉伯人相比,在像医学和化学技术这样的领域,他们都还是粗野和无知的;他们还没有达到制造阿拉伯人的“希腊火”的水平;到十字军东征结束时,拉丁人才第一次拥有了差不多平等的地位。
正如我们看到的,著名的帝国西进运动,消失在文明向各个方向的普遍扩张中。在很大程度上,西欧与苏丹或马来西亚一样,也是一个边缘地区,虽然与这两者相比西欧的城市和文字文化更早地发展起来。与它们一样,它也从属于更加古老的文化中心。就像在苏丹和马来西亚一样,文化知识的流动是严重一边倒的——从中国、印度、中东和(主要是)地中海东部流向西方国家,而向相反方向的流动是极少的。在很长时期内,这甚至也反映在地区间的贸易中。与南方和东方的其他边缘地区一样,西方世界主要提供自然资源,包括奴隶,而不是完善的制成品。相应地,西方世界的一些地方性事件——地方性城市化与知识的兴衰——对于整个世界也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中世纪的伊斯兰作家非常了解拜占庭、印度和中国,但是他们对于远西的兴趣并不比对于西藏或东非更大,当然与远西有直接联系的时间和地点除外。欧亚非大陆这个历史大舞台的主要特征及其“主流”——如果有的话——很少受到这些边远角落的事件的影响。
也许西方世界的边缘位置使它受益,这有些类似于大体同一时期的韩国和日本,它们同样远离了跨地区交流的主要线路。在这片处女地上,西方人能够依据古老的文化主题发展起独立的不同的文化,不大会被常常肆虐在从爱琴海到孟加拉地区的文化和军事骚乱所干扰。而且,在中世纪晚期之前,西欧人在文明既有的界限之外总有一些吸引人的空间,并把活动范围扩大到那里(而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缺少这些)。要探寻西方的特性,很多时候也许应该从其边缘位置来寻找。无论如何,把西方国家与其他边缘地区——它们与核心文化区形成不同——相比较,也许比把它与那些核心地区相比较更有成效;比如,可以比较当地的创造性与接受外来影响的能力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时,单单给予“东方”社会——或者因为它们自身的重要性,或者因为对欧洲的影响或贡献——更多的关注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学会把西方国家看作进入更广大的历史进程的众多社会中的一个,这种进程在某种程度上超然于甚或是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虽然西方是相对孤立的,但是,进入这些更广大的历史进程甚至对于西方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来自其他某一社会的影响或借鉴的数量,甚至不能简化为由于它南面或东面强大的邻居出现而带来的更普遍的积极和消极的后果。通过这些邻居,广泛的跨地区模式最终在任一特定时期都设定了一个限度,限制着西方或西方的任何一个社会所能接受的外来影响的可选择范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