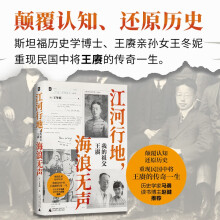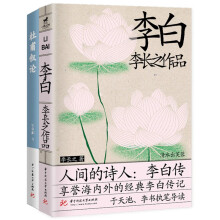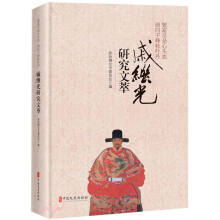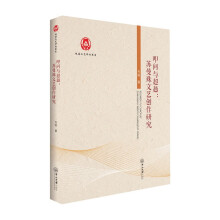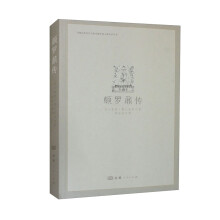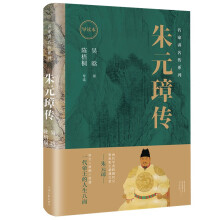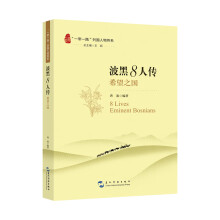纸上苍生而已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本书交稿时,那个晚上的情景。
夏末,结束所有文章的整理工作后,我拎着电脑包,离开了咖啡店。
彼时,已经将近夜里十点。江南夏末的风,终于在深夜时分有了一丝凉爽。整条街上,只有我穿的高跟鞋的“嗒嗒”声在回荡。
然后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因为激动?因为辛苦?还是因为梦想终于达成?
不,都不是。这并不是结局,而是我写作路上的一个序章——当我的心给出这样一个答案,我擦去眼泪,笑了。
是的,出书永远不是我的梦想。我只是爱写,只是想写,仅此而已。
我的第一本书《平生》,记录了社会底层人物平凡又艰辛的一生,而第二本书,则记录了清朝十一位妃嫔和两位公主的一生——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一边是青鞋布袜,一边是凤袍凰冠;一边是暑雨祁寒,一边是荣宠万千。草屋深宫,地下天上,都在同一个人间。
再细思量,心中又生出几分凄凉。
任你金枝玉叶,富贵如花;任你锦衣玉食,圣眷优渥,孤单终结一生之时,回望看到的,不过同一轮陪伴万物的伶仃的月亮;抬首所见的,不过同一片接引众生通向黄泉的曼珠沙华。
活着,无不艰难,无不苦楚,当我完成这两本人物身份截然相反的书后,我发现,人之一世,命不同,运相异,最终却是殊途同归。
倒真如龚自珍所说:“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
在写这本书时,我写的第一个人物是王敏彤,即完颜立童记。
写她是因为我看到了另一篇关于她的文章——与其说是文章,不如说是将百度上的内容拼凑起来的人物介绍。当时一个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王敏彤终身不嫁,究竟是因为一生痴爱溥仪,还是因为不愿意降低格格的贵胄身份。
为了令读者感慨唏嘘,太多文章将王敏彤的终身未嫁归因于对溥仪的痴爱,说她爱上溥仪,甚至是在表姐婉容之前。但溥仪与婉容大婚之时,王敏彤才十岁。十岁女孩将对溥仪的爱深藏心底,直至终老——未免有些太不写实。
带着这个疑问,我翻查了很多资料。我认为王敏彤作为真正的皇亲国戚,作为格格,她身上有着平民女孩所没有的清高与孤傲,她不愿,也不能下嫁。
因此当王敏彤年老后,溥仪的另一个弟弟亲自登门,表示愿意与她登记结婚时,她说:“我不能一生都在北府兄弟圈里打转。”
与爱无关,与眷恋无关,与辜负更无关,只是与阶层,和不肯放下的格格身段有关。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在从沈阳北至上海的K190次列车上意识到这一点的,然后我在手机的锤子便签上写下了这篇文章。
彼时,我的第一本书《平生》,还未交稿。
之后,我便对清后宫的金枝玉叶们产生了兴趣,到底电视剧中演绎的她们的一生,是不是真实的呢?
当然,我所写的,也未必都是真实的。不过关于她们的命运主线,不会有戏说的成分。
比如《还珠格格》中五阿哥永琪的母亲愉妃,她其实是在永琪早夭后,心如枯井地活到了七十九岁;
比如慈安,并不如众多影视剧中表现的那样懦弱无能,她的气度格局皆在慈禧之上;
比如慧贤皇贵妃高氏,她多次被超拔,并不如世传那样,是因为深受乾隆皇帝宠爱,而是因为皇上想以此激励其父兄为朝廷效劳,最终,她的父兄皆死于乾隆皇帝之手;
比如与皇帝离婚的第一人文绣,她其实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在这本书里,也记述了两位宠冠后宫的清妃,一个是皇太极的最爱海兰珠,一个是顺治皇帝的最爱董鄂妃。无奈情深不寿,慧极必伤,此二人都在最当芳龄时因丧子郁郁而终。
因此,这本书不是戏说,也不能归于正史。它是在梳理了十三位佳丽的一生后,融入了个人的情感与理解,我从她们的最始,走到了她们的最终。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每写一个人物,都要根据她们的命运及结局,大致揣摩出她们各自的性格。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代入其中,一次又一次地走进紫禁城。身边,是红墙黄瓦;抬头,是狭窄的一片蓝天。
这也是写人物最艰难的地方,入戏容易,出戏难。待她们驾返瑶池,我也仿若大梦初醒,活完了一个女人的一世。她这一世的期待,热爱,悲凉,寂寞,甚至绝望,我都半点不差地一一体验过来。
重新回到现世,就像是从孟婆的那碗汤中回过魂来,之后,便是长久地怅然若失。
不容易,她们每个人的一世,都不容易。
身入后宫,无不是浓墨重彩地开始,收梢却轻描淡写——即使死后获得哀荣,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有一切,统统与爱无关。
这本书交稿时,我的心情很是平静。因为我知道,尽管只是纸上苍生,也是永写不尽。我愿意将本书,交与你阅读。愿我们在别人的故事中,活好自己的一生。
此后,我将继续铺卷落笔。
斯为序。
苏小旗
写于夏初一场大雨后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