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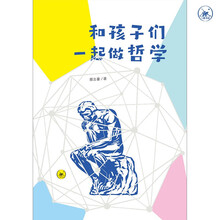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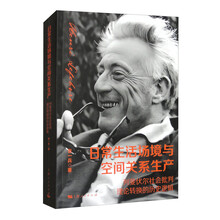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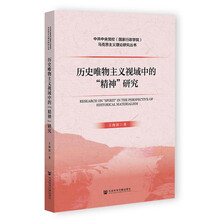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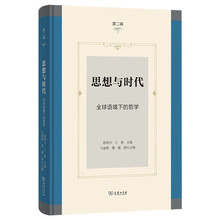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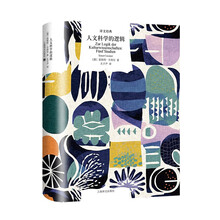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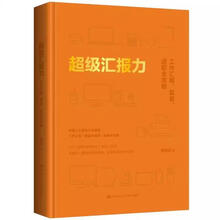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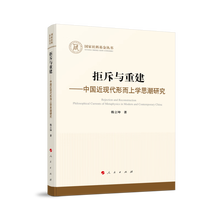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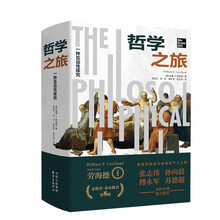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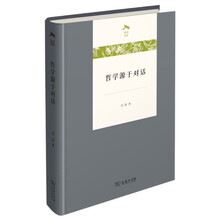
“作”就是创新,孔子讲“述而不作”,是强调继承传统而否认人为创新——这与早期中国文献中存在的一些论调很相似,即认为被人为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坏东西,比如战争、兵器、刑罚,而圣人是“述而不作”的,坏东西都不关圣人的事。但不创新、不造作又怎么有发展?
到了秦汉时期,创新的历史焦点汇聚到了中央集权帝国这种新兴的制度上,由是才有儒家与秦始皇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不是一时间才激化、出现的,实际上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普鸣通过梳理这个历史过程,揭示出了“创新”“造作”为中国历史进程带来的文化张力。
作者,起也。“作”有兴起、创新之义,但孔子却讲“述而不作”。是“述”还是“作”,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中围绕“创作”“人为”观念展开的一场历史悠久的论辩。“述作之辩”不仅是哲学层面上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呈现,其核心在于大变革时代人们对新制度——中央集权帝国——合理性的阐释,体现出“创新”为中国历史进程带来的文化张力。
此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普鸣的代表作之一,由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作者追溯并分析了商周卜辞铭文、战国诸子文献及秦汉政论中有关“创作”的叙述,不仅延续了西方汉学对“关联性思维”的探讨,也为考察中国古典文明提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视角。
司马迁笔下的早期国家历史
黄帝之治
开篇,《史记》便描述了国家的兴起。《五帝本纪》篇末“太史公曰”总结自己对于往圣的记述时,强调自己将现存材料搜罗殆尽,去除其中“不雅驯”的因素。据此,许多评论者解读《五帝本纪》之时,以为司马迁是在将早期神话“理性化”及“历史化”。
相反,笔者以为,这并不仅仅是在试图以理性化、历史化的方式去记述往圣。司马迁写下这段叙述时,心中自有旨意。与他处相类,司马迁在此并不仅仅是在尽量客观地描绘历史:他打造出这个故事,乃是为了提出各种各样与历史过程相关的问题。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讨论了各种与国家起源有关的叙事。在此,司马迁将之再度演绎,而我们必须探讨此举背后的原因。因此,阅读这一故事的每一步都需要追问:何以司马迁选择如此叙述?
司马迁以神农统治之衰落入手:“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恰如此前所述,公元前3世纪的叙事利用神农这一人物指代动乱出现前的和平时期,《商君书·更法》《画策》便是一例。换言之,这一和平年代出现在暴力被引入之前,此后黄帝创作国家,将暴力纳为己用。诚然,我们在此看到了动乱随着神农氏凋敝而兴起,可与《商君书》二篇相似,《五帝本纪》也没有试图解释动乱的起因:在司马迁笔下,暴力既非蚩尤所作,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与《商君书》二篇相似,暴乱之所以兴起,都仅仅被视为历史变迁中的一部分。
继而,司马迁笔锋一转,说黄帝企图控制这种动乱:“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神农无法攻克诸侯,黄帝则能正确使用武力使之归顺。《商君书》二篇将神农、黄帝之别描绘为一位和平君主与另一位国家创制者之别;与之不同,在《五帝本纪》中,同样是面对暴乱的兴起,神农与黄帝一个无能为力,另一位却能处理得当。
这里同样值得指出,“征服成功”指获得诸侯的拥戴。换言之,黄帝胜利之后,地方诸侯显然仍然存在。是故司马迁并未给出一套鼓吹创制中央集权,以此废黜诸侯的法家叙事。
动乱既已发生,黄帝既已用武,至此蚩尤才出现在叙事之中:“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动乱、武器皆非蚩尤所作,二者都先于他存在,司马迁也没有联系创作问题对二者展开讨论。相反,蚩尤被当成最为暴虐、最难对付的诸侯。
然而,在进一步讨论蚩尤之前,司马迁引入了另一位敌人——炎帝:“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如果说蚩尤还是诸侯中的一员,只是拒绝臣服于中央朝廷的话,司马迁则将炎帝描述为意欲篡夺所有诸侯权力之人。
到了这个关头,司马迁才开始讨论黄帝对万物的条理、组织,上述的许多思想家都以条理、组织定义圣人之业:“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此时此刻,黄帝已做好了清除乱贼的准备。先除掉炎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然后消灭乱贼蚩尤:“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此处所谓“蚩尤作乱”并非如《吕刑》所言那般,认为一切暴乱始于蚩尤,而是更接近《十六经》的看法,认为蚩尤发动了一次具体的暴乱。然后,诸侯辅佐黄帝击溃乱贼:“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黄帝如此击败炎帝、蚩尤以后,终于使得诸侯将其奉为天子,继神农之业。此后,他继续凭借武力维持秩序:“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
因此,整个叙事围绕着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展开:始于神农对诸侯之束手无策,终于黄帝获得诸侯拥戴,受其承认而成为新的天子。如此处所言,成功统治之钤键,在于君主须能控制诸侯,却不篡夺其权力。
司马迁以黄帝与乱贼炎帝、蚩尤的关系来强调这一点。在他笔下,炎帝、蚩尤二者互相补充:前者轻侮地方权力,后者无视中央权力。如果要阻止对诸侯权力的篡夺,黄帝就必须击败炎帝;如果要遏制神农末世大行其道的暴乱,那他也必须击溃蚩尤。炎帝的重要性在于,当他威胁篡夺诸侯权力时,诸侯恰恰能够投靠黄帝;蚩尤的重要性在于,当他与中央朝廷抗衡之时,黄帝得以成功率领诸侯与之相抗。是故黄帝被诸侯奉为下任君主,首先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既要展示自己有能力引领诸侯,又要保持对诸侯地位的尊重。与《商君书》大异,此处之黄帝绝非中央集权国家的创作者,而是封建体制的支持者——在此封建体制之中,诸侯的地方权力与君主的中央权力维持了平衡。
不仅如此,黄帝条理、组织,却不创作。叙事也并没有让他的两位对手负责创作,只让他们分别代表了两个极端,而黄帝为了正确地组织运用国家武力,必须维持两极之间的平衡。所有人都与创作无关,包括黄帝和蚩尤;黄帝从未创作新事物,也没有将蚩尤所作的任何事物据为己用。在关涉有组织的暴力的黄帝—蚩尤叙事中,制作兵器的问题极为关键,但司马迁对此事绝口不提。相反,他意在表现黄帝能有效用兵,以挟制诸侯。此事关乎正确地使用暴力,而非制造暴力。虽然司马迁说神农末世暴乱出现之后,黄帝立定了秩序,但有一点含糊不清:在黄帝成功施行秩序的过程中,其所作所为,哪一条不是神农原本应该能做的?他没有引入什么新东西,乱贼亦然。
这点很有意思。因为在叙述国家兴起时,许多作者以为,圣人只是在条理、组织,在观念上反对圣人所制的国家包含任何的造作、强制因素。然而,笔者并不以为此处司马迁意在介入一场关于国家最初起源的思想论辩,或者更确切地说,司马迁此举仅仅有助于他处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他主要关心对所谓“国家”给出一个定义,使他得以衡量后来的历史发展,包括将帝国引入中国历史的问题。正是在讨论进入帝国的时候,司马迁转向了创作问题,如果黄帝组织的封建制度标志着国家的基本形态,那么,进入帝国将标志着一种彻底的断裂:换言之,传统上,地方与中央力量相互平衡,而帝国的引入则意味着一整套中央集权统治的引入,为传统画上了句号。因此,我们在第三章详细讨论的主题,被司马迁极为复杂地重构。而《史记》开篇第一节便迈出了重构的第一步,占据了大量的剩余的讨论。
致谢
译者例言
绪论
对中国文化的分析
研究方法
研究架构
第一章 御疆辟土
青铜时代对祖先与创作的看法
青铜时代的《诗》与卜辞、铭文
周之衰亡
结论
第二章 人之技艺
战国时期对自然与文化问题的论辩
论辩之始
修正对“自然”的定义
文化的本质:战国后期论辩的发展
结论
第三章 圣人、臣下与乱贼
叙述国家起源
早期中国神话研究的症结
叙述国家起源
结论
第四章 创作帝国
帝国统治的兴起与巩固
创作帝国:秦朝
帝制的衰落
汉代对帝国的再造与巩固
结论
第五章 创作的悲剧
司马迁对帝国兴起的重构
司马迁的规划
司马迁笔下的国家历史
引申
结论
附录“作”字探源
参考文献
索引
温馨提示:请使用太仓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