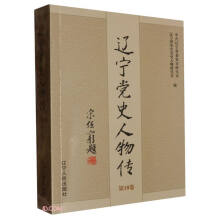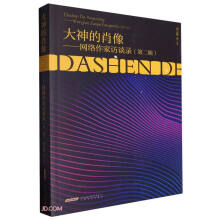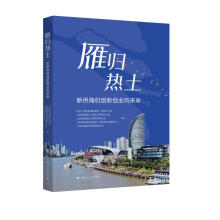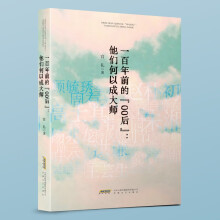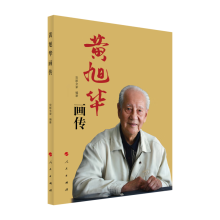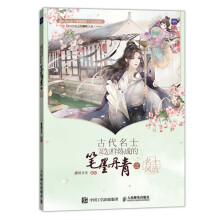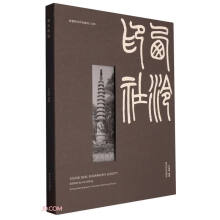《石门博士(第一卷)》:
陈金芳,女,1962年12月出生,石门县蒙泉镇李耳岗村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理论所教育制度研究室主任、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道尔顿教育协会专家组成员,华夏道尔顿教育体系(中西合璧)创始人。研究领域为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高考招生制度改革、道尔顿教育等。近年来主持了多项省部以上研究课题,是新中考、新高考问题专家,中小学选课走班制首席专家,中国教科院实验区教改指导专家,指导了包括北大附中、复旦附中在内的多所中小学的教改工作,取得了瞩目成效。近年来出版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素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选课走班:新时代中小学教改实践的必然选择》《道尔顿教育计划》(译著,北京出版社已第七次印刷)等学术著作,在《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人民教育》《光明日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读博感言
我1980年高中毕业于蒙泉中学,同年考入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84年本科毕业后先后在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和中南大学任教12年,于1996年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毕业,毕业后留京工作。我考博士纯粹是出于压力和偶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高校教师已开始强调高学历,我却因为结婚生子耽误了读研时机,在高中同学张耀南(他那时正在北京大学读博)的建议和鼓励下,我以同等学力资格直接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泰斗黄楠森先生的博士生,理由是据说他老先生招学生不重男轻女,后来我成了1996年那一届北京大学哲学系众多专业博士生中的唯一女生,被戏称为“陈独秀”(意即“一枝独秀”,本人姓陈)。那时候全国招收博士生数量较少,大学里往往由几个导师组成一个小组指导一个博士生。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北大有三位大师指导过我,校外还有两位大师也是我博士论文指导小组的,一位是中央党校的崔自铎先生,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袁贵仁先生(后来成为教育部部长)。这些先生都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杰出人物,我在三年读博期间受益匪浅。
我记得上本科期间是比较轻松的,背点别人的东西就可以通过考试,抄点别人的东西(只要抄得巧妙)就可以通过本科毕业论文。上了博士才真正体会到独立思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则,既通不过考试也通不过毕业论文。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96—1999),我参加了黄楠森先生主持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人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在导师的指导下承担其子课题“人的素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很大:“论人的素质”,并非从生理解剖角度,而是从哲学层面上讨论关于人的素质的内涵、外延、特征、实现途径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博士论文要求自成体系且能自圆其说,个中滋味难以言表,颇伤脑筋。三年下来,窈窕淑女变大妈。记得刚入学之际,有人调侃我说:女人读哲学博士,简直荒谬,等于双向损害!意思是,女人损害哲学博士,哲学博士损害女人。我有没有损害哲学博士不好说,总算凑合毕业了,虽然始终也没有学明白;哲学博士损害了我的确很实在。从此我的思维更加理性甚至僵化,从前文艺青年的气质似乎消失殆尽了,自然就不那么有趣和可爱了。不仅外表跟气质受到损害,家庭生活跟亲子关系也受到较大影响。当时我在北京读博,先生和儿子在长沙的中南大学(当时是中南工业大学)生活,先生身体欠佳,经常闹病;儿子处在成长的重要时期(8~11岁),缺少沟通和陪伴,这是我心底永远的痛。对于女人来说,读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个人发展而言,读博当然更好;但如果为了个人发展而影响了家庭和谐及孩子的成长甚至社会的发展就得不偿失了!社会上对女博士有偏见,曾经将女博士列为第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女博士不好找对象,因此造成终身不婚不育,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损失啊!好在我当时已经结婚。其实,读博并不代表能力、成功甚至博学,它只是代表一个学业层次,代表某种专业工作的门槛。当然也会有人将其当作功利筹码或虚荣的装饰品。
读博虽然有得有失,但的确让我开了眼界、长了才干,拥有了更加广阔的生活,磨炼出了更加强大的内心!如果有来世,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读博、当博士。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