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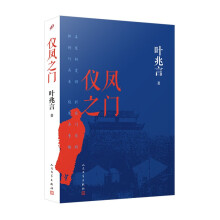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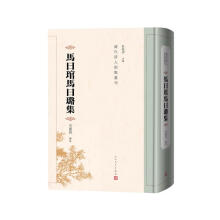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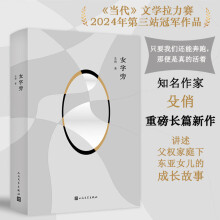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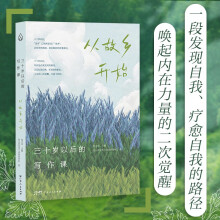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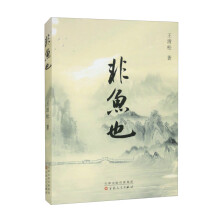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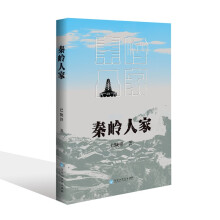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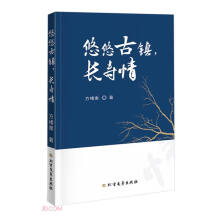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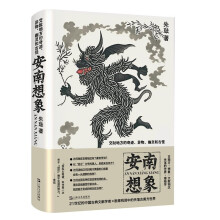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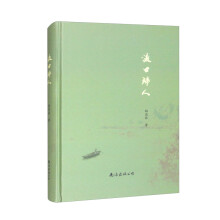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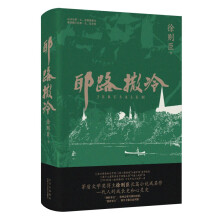
本书“人民文学·紫金之星”文学奖、“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等奖项获奖者董夏青青的力作。作者董夏青青以冷静的笔触、克制的情感刻画了戍边官兵们面对高寒艰险的生存条件时的内心流动,呈现了士兵们拒绝庸常、回归崇高的蜕变。董夏青青的作品一直为全国作家、评论家、编辑和广大读者所关注。其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强,兼具阅读与鉴赏、研究与收藏价值。
小说卖点在于小开本,便于携带,有效填充大众读者的碎片化时间,机场候车、乘坐地铁等时间段,读者可以抛开手机进行深入阅读。当代作家的中篇不仅带有时代性、现实性,而且可以使读者站在小说阅读的最前沿,了解小说这种文学发展的新契机,对阅读时间、场地的要求进一步减少,鼓励大家去阅读,也符合国家全民阅读的号召。
这本书是百花社倾心打造的一款可以成系列的既长销又畅销的中篇小说单行本。依托《小说月报》的号召力,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作者新近刊发的有寓意、有思想、有内涵的中篇小说单行本。
本书稿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在高原冻土之间、在祖国的边境线上,戍守士兵许元屹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壮烈牺牲,战友们在他衣袋里的烟盒上发现了他留下的简短的家书,家书中简单地记录了他身为一名士兵的自豪。许元屹的去世不仅持续引发战友们的伤痛,更催生了所有人重新思考与自己所关联的一切事物。小说中“许元屹”不仅是一个人名、一个人物,更是一种象征、一种信仰,作者通过许元屹个人的选择与气节,表现了戍边官兵保卫家国的崇高品格与英雄情怀。
“许元屹的妹妹,跟她爸妈一块过来了吗?”他问教导员。
教导员想都没想就答了他:“没有,没过来。”
“他爸问许元屹一个月工资多少了吗?”他又问。
“没问。”教导员告诉他。
“他一个月工资多少没告诉他老子吗?”教导员问他。
他摇头,小声说了句许元屹拿钱在供妹妹上学,妹妹在师范大学读研究生。
教导员嗯了一声没再多问。他把烟熄在喝空了的矿泉水瓶子里,烟头碰着瓶底的一点水,吱了一声。两人空坐半晌。
把许元屹带的上等兵送到教导队后的第二天下午,教导队的队长打来电话叫他赶紧过去一趟。
那天正好赶上县城疫情封控,出租车停运,院子里的车没有提前批示用车手续的也没法动,他便步行从医院往教导队的营院走。途中路过一家小饭馆,门脸十分熟悉。他站定想了想,记不得究竟是自己在里面吃过饭,还是见谁在朋友圈里发过。
到营院门口,教导队的队长正等在那里。往宿舍楼走的路上,队长跟他讲,分区的心理医生正在给上等兵做干预治疗,每天中午做一回,预计得持续半个月。
他问队长:“上等兵进营院大门之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崩了?”
队长说,上等兵昨天晚上排在队列里进食堂吃饭。因为是周五,食堂会餐,炊事班熬了羊汤,炖了肘子和酱牛肉,主食有拌面、炸馍、手抓饼和小蛋糕,饮料除了酸奶还有果仁奶和奶啤。上等兵没等打上饭,抱着餐盘蹲在地上大哭起来,说自己班长临走时饿着肚子,从早上起来到下午人没时就咬了两口压缩饼干。
晚上熄了灯,有战士去水房洗漱,看见上等兵站在水房的镜子跟前鞠躬,一边鞠躬一边反复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战士把情况报告给队里,队长晚上把上等兵带到自己屋里,想跟他说说话,可上等兵进了屋一声不吭,只呆着发愣,过会儿说困了,想睡觉,队长就把他送回了屋。
第二天一早,和上等兵同屋的战士过来找队长,说起床号响了以后,他们都着急穿衣服、扎腰带准备下楼跑操,只有上等兵不紧不慢,穿戴齐整了站到阳台上开始打敬礼,自己喊,敬礼!然后啪地立正打一个敬礼。他们把上等兵拉回屋里,上等兵就自己在屋子里倒着走来走去。
站在队长宿舍门前,他隔着门上的透明玻璃向里看。上等兵佝偻着身子坐在两张床铺中间的书桌前,面朝窗户。在他身侧,床沿上坐着一位年纪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女人,正同他讲话。
小屋里,从上等兵面向的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让他想起年初在山上的团部营区,还没有进沟的某天。
那天吃过午饭,他和军医、营长、许元屹在医务室里烤电暖炉、抽烟。正聊着天,上等兵进来了。上等兵说自己养的狗病了,好几天不吃不喝,总拉肚子,想找军医给开点药。
军医说:“现在开药都得开单子,人好说,给狗怎么写?”许元屹往军医嘴里喂了根烟,点上火说:“你该咋写咋写啊。”军医坐到办公桌前拿出一张医药单,瞅着上等兵说:“那你说,照你说的写。”
“姓名?”军医问。
“花虎。”上等兵回答。
“性别?”
“男。”
“年龄?”
“三个月。”
“单位?职务?”
“单位……勤务保障连?职务……看家的。”
“提提身价,给它写保障处吧。”军医说,“然后科别和保障卡的账号花虎都没有……”
“病情及诊断?”军医又问,“我说你给它下的啥诊断?”
“拉肚子。”上等兵回答。
“那就写腹泻。”军医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写,“先给开一周的甲硝唑氯化钠注射液吧。”
“哎,你。”军医抬头又瞅了上等兵一眼,“知道怎么给它打针吗?”
“我会,我练了。”
“在哪儿练的?”
“我拿自己练的。”上等兵说。
尽管上等兵此时背对着他,脸低得快挨到桌面,但他仍能清晰想见上等兵的神情。正如那天中午,上等兵一板一眼地回答军医接二连三提出的问题。事关生命存续的问题。
从教导队回到分区医院时已近傍晚。他爬上二楼值班室,推开门见教导员正盘腿坐在办公桌前对着摊开的笔记本出神。
“那孩子没啥事吧?”教导员见他进屋,松开咬在嘴里的笔。
“强制心理干预,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他说,“老团长他们上山了?”
“吃完午饭就走了,这会儿快到兵站了,应该能赶上晚饭,”教导员趿拉上鞋,身子转向他,“有意思吗你说,这是老团长被调到野战师当副参谋长以后头一次回咱团里。”
“你感觉呢?”他说,“这回指派他上去是参加谈判吗?”
“司令肯定会让他参与,”教导员说,“那边就有他认识的,都打过多少年交道的。那个死胖子又升了军衔,据说二老婆又生了个儿子。这回要是副参谋长见着死胖子,谈也肯定想好好谈,可想到许元屹还有受伤的弟兄们,肯定想扇他,至少要威胁他们两句吧?”
“再有,估计也考虑到了让他上去把握分寸。咱们和他们,就是之后上来的人……两拨人就跟斗牛和耕牛一样,培养目的和评估标准都不一样。现在这种情况必须两条腿,但首先这两条腿得稳当、得协调吧?他不是总说嘛,只要不是打仗,当主官的就别把下面的兄弟带病了、带残了、带没了、带监狱里去了,尤其把冲动和血性分清楚。别学那边的人,拿弟兄们的血给自己贴金。”
温馨提示:请使用沧州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著名作家班宇说:“《冻土观测段》不是一篇可以轻易踏入的小说,这并非在说其叙述方式始终抗拒着读者,当然,它也无法被归纳为某种河流式的涌动描绘——毕竟一具遗体曾在此处悬停,没有新的工具和语言,能够完整解释如此迫在眼前的如同障碍一般的残酷与沉默。进入小说的难度在于,如果我们熟悉董夏青青的小说,那么在这里,势必要摒除一种幻游者的视距,不是幽灵引领着我们去徜徉和重新发现,不是对于圣者或好人的再次解释,而是需要成为被邀请的观测者,同时处于真实的内部和外部。位置本身即构成她的最为强力的修辞。”
青年文学评论家冯祉艾说:“‘冻土观测段’是一个包含多种艺术内蕴的意象,‘观测’本身即是一个具有观照意味的词,观测可以有多种视角,平视、俯视、仰视,观测还可以有多个对象,被观测者、观测者,而这些视角和对象又并不都是固定的,甚至作者和读者之间也形成了某种观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