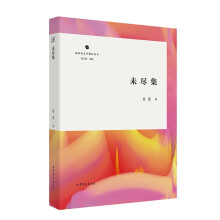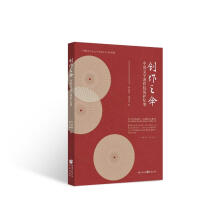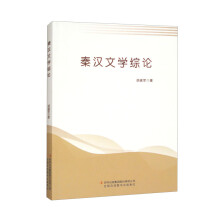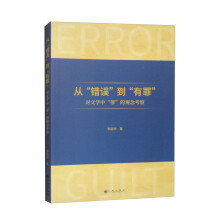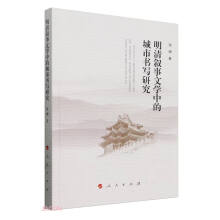行为艺术:读《奇骗》
袁枚这人,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清代乾嘉年间的社会名流,读书人的楷模。后人为他冠名: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美食家。前面三个“家”,老侯都没觉得有多稀奇,可头戴美食家头衔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人不吃饭不行,可你瞅瞅《随园食单》,看人家袁枚怎么吃,
再瞅瞅咱的餐桌,嗨,不说也罢。
袁枚的住地叫随园,时人称他为“随园先生”。老侯对随园先生一向比较喜欢。喜欢他的“性灵说”。我读过他不少作品,《小仓山房文集》中的一些,《子不语》中的一些,还有《随园
诗话》中的一些……特别是《随园诗话》,一度是老侯的案头书,每晚伴我度过睡前的那段惬意时光。
我在笔记小说《老僧镜澄》中写到袁枚。说,乾隆年间,南京小仓山水月庵主持镜澄,喜欢写诗,且写得好极好极,却四十年间与山下的随园主人,大诗人和大诗评家袁枚素无往来。这位袁先生有一怪癖,家中四面不设围墙,园中四季花木景致,都向游人敞开,要来便来,要去便去,跟今日的公园近似。镜澄的朋友老吴,一日畅游随园,与袁枚偶遇,交谈甚欢。谈话间,老吴背诵两首镜澄的诗,袁枚连连称好。老吴傍晚回到水月庵,跟镜澄说起白天的奇遇,随后有了这样的情节:老吴站着跟镜澄说话,满脸喜色,告诉镜澄,随园先生,夸他的诗好。什么诗?《留澹川度岁二首》嘛。这诗,老吴几乎每天都要摇头晃脑吟诵一番。
老吴模仿随园先生的行状,点头,说一个好,再点头,又一个好,三点头,又又一个好。
老吴口中啧啧有声:“一连三个好啊。”
随园先生喜欢镜澄的诗,不奇怪。先生有话:“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镜澄的诗,正是以性情动人。
谁知镜澄听了老吴的话,只是嘴角稍稍一动,随后闭上眼睛,口中喃喃,不再搭理老吴。
老吴赔着几分小心说道:“要不,明天我陪你下山,拜访随园先生?”
镜澄慢慢睁开眼睛,吐一口气:“老僧出家四十余年,不曾踏入随园半步。”
老吴心说,人家随园先生,名闻天下的诗坛伯乐,平日喜称人善,有“广大教化主”之誉,可谓“当代龙门”,你镜澄拜访一下,等于跳了龙门,岂有不去之理?
镜澄似乎看透了老吴的心事,缓缓说道:“和尚自作诗,不求先生知也。先生自爱和尚诗,非爱和尚也。”
你说这老僧镜澄,是不是很有个性?
小说的结尾,是某年某月,随园先生闻知老僧镜澄之执拗,呵呵一笑,说:“和尚不必来,不必不来。”
不谦虚地说,老侯觉得这篇作品有点意思。同时老侯还觉得,袁枚笔下的微型小说《奇骗》,比老侯的《老僧镜澄》更有意思。 说来好生惭愧,老侯前不久才知道,袁枚写过一本志怪小说集《新齐谐》。这里我要说的《奇骗》,就是出自该书。
《奇骗》写了一个连环骗局,与美国系列电影《谍中谍》有些类似。主要人物有四个:金陵老翁、钱店(银行)店主、送信少年、看客(文中称之为“客”)。老翁拿银子去钱店兑钱,为银子的成色,跟店主喋喋不休。这时一少年走进钱店,称老翁为“老伯”,说真是赶巧了,我是你儿子的同事,你儿子托我带家信和银子来了。交毕,“一揖而去”。
老翁拆开信,对店主说,我这老眼,看不清啊,你帮我瞅瞅。店主读信,都是家常话,最后一句说,给家里带了“纹银十两”。老翁很高兴,对店主说,把我的银子还我吧,不用计较成色了,我儿子说他给我十两银子,就用这十两换钱吧。店主将银子称重,却是十一两多,顿生贪心。信上不是说十两嘛,就按十两换钱好了。老翁刚走,店中一位看客提醒店主可能被骗。店主剪开银子,果然是铅胎假银。在看客指点下,店主追上老翁,与之争执。周边的人问怎么回事,店主说如此这般这般,并拿出假银给大家看。老翁说这银子好像不止十两,不是我的。一称重,果然不止十两。
众人责问店主,“店主不能对,群起殴之”。这是老侯所见的骗子故事中,最具智慧含量的一例。哪是行骗啊,简直就是行为艺术,其行骗的目的,从物质层面一跃而进入到精神层面。
老侯从没见过这般爱惜羽毛的骗子。比较而言,当代骗子,都形而下得很,渣得很。
老翁成功地运用店主的贪心,以团伙作案的方式,为自己洗刷了骗子的名声。严格说来,那店主,不也是一个骗子吗?骗子把骗子骗了,是本文的一大亮点。
此外,这篇作品中蕴含的故事逻辑,也无懈可击。以看客为例,店主要他带路去找老翁理论,他不肯去。不肯去的理由很充分,我跟老翁是邻居嘛,弄这事,不是结下仇了?店主再劝,还是不肯。非得等店主“酬以三金”才勉强答应带路。远远望见老翁在酒肆喝酒,便对店主说:“汝
速往擒,我行矣。”这位看客在事件行进过程中的一言一行,都合情合理,毫无破绽。而且呢,又随手骗得“三金”。
别的话不说了,老侯只想在四个“家”之外,为袁枚先生再戴一顶“小说家”的帽子。他老人家爱戴不爱戴都得戴,就这么定了!
延伸阅读:
奇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