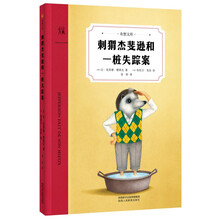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偷着乐的小时候/我的小时候》:
一 夜晚
小时候,我和两个弟弟在一些方面很对脾气的,比如我们都不喜欢玩得好好的却突然被催着去睡觉。
我的妈妈在有的事上很糊涂,可在催小孩睡觉这一点上却永远很清醒。
妈妈一催,我们只好一肚子怨气,乖乖地去躺到床上。妈妈会来检查,好在她检查起来很马虎,只是望一眼,只要我们闭上眼睛了,哪怕眼皮还在动也不追究。
我和两个弟弟各睡一张床,我那张床是帆布床,中间凹下去,睡觉时感觉像在小船上晃着,睡不着的时候,就很想把弟弟们也推醒。正想着要尖叫一声吓一吓他们,却听见从他们那儿传来哧哧的笑声,没开灯就知道他们也想兴风作浪。
于是我们发明了许多玩法,不用开灯,也绝不发出大声响。比如我们会把两条席子卷成筒形后接起来,做成一个地道,从地道里钻进钻出;或是把拖鞋当炸弹扔来扔去,这样,摞起的被子堆就成了现成的掩体;有时就干脆练倒立,一律头朝下挂在墙上,这时假如妈妈推开门,一定会吓得昏过去。
我们最疯狂的一次玩法,是把帆布床四个脚扎紧后吊起来,当作森林吊床。我躺上去刚想享受一番,突然咚的一声,连人带床掉下来,我以为我会摔昏的,但却没有昏,而且敏捷得很,在妈妈的拖鞋声由远及近时,我已像模像样地躺好了。
最适合的玩法是打开台灯演无声电影。床是银幕,大家轮番上去表演,不用台词,也不需要情节,一会儿演一个残疾人,一会儿演独臂大盗,有时还能一跳一跳地演动画片。亏得窗帘是拉着的,否则过路人会以为屋里在闹鬼。这种玩法是最文雅的,不用担心会惹出大乱子,最大的麻烦是笑声压不住,于是我们就发明了一种毛巾口罩,把毛巾毯叠成一厚摞,一笑就用它捂着。
反正,这成了发挥智慧的游戏,有时一到天黑,弟弟就会嚷,快睡觉吧!他觉得公开的游戏不如秘密的游戏开心。
妈妈起初觉得奇怪,因为过去她的孩子听到她催睡觉去,总是满脸不快,如今却像吃了瞌睡药一般,动不动就张开嘴打个哈欠作引子,然后嚷:想睡觉了。
妈妈至今没找出其中缘由,她虽然像是无事不通,可却仍有这破译不了的谜题。
二 长辈梦
小时候我发疯一样想成为大人,做长辈,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各种权利:可以有装秘密的抽屉,带着暗锁;钱袋里永远不会是空空的;可以竖起指头同小孩们谈自己的高见。特别想当的角色是妈妈,因为妈妈能决定孩子星期天去哪儿,能随便开食品柜,能戴戒指、穿丝袜,能同爸爸一块儿去参加别人的婚礼。这些都是我梦想的事。
我没找到过教人做妈妈的书,可是我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最初,是做了布娃娃的妈妈。那个布娃娃叫阿婷,圆脸红裙,我会给她编八条小辫子,乍一看,就像头上排了电线,还用彩纸给她做过一条披巾。可惜摆弄多了,她的胳膊掉了,再后来头也不知去向,变成个无头独臂的怪胎。阿婷消失后,我再也不想要布娃娃了,觉得意思不大,因为布娃娃太省事了,不需要催她快把汤喝光,也不需要叮嘱她别睡懒觉、别忘了带手帕。一天,住在我家楼上的小燕来求我给她编小辫,我突发奇想,说给她当一小时的妈妈。
小燕那时候就和我很谈得来,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她爽快地答应了,像真的一样,一口一个“妈妈”地叫,但在这亲爱诱人的称呼间加入了许多新要求。
“妈妈,右边的辫子重编,太高了。”
“妈妈,把你的紫色蝴蝶结给我用用。”
“我口渴得很,妈妈,有没有酸梅汤?”
“你手太重了,怎么搞的?妈妈连这都不会做!蝴蝶结皱了。”
我这一小时的实践吃足了苦头,让这娇“女儿”指挥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她刚想让我洗盛酸梅汤的茶缸,我跳起来大叫:“时间到了!”
我怂恿小燕也当一小时的妈妈,想让她也尝尝被使唤的滋味,不料她毫不犹豫地说:“我一辈子不做妈妈,我怕小毛头撇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