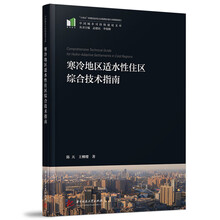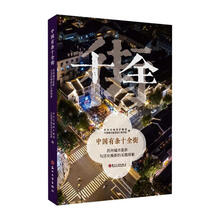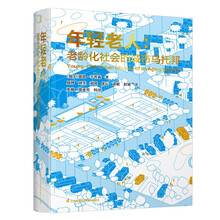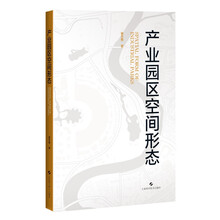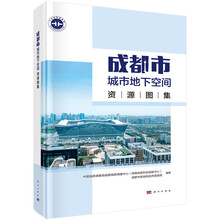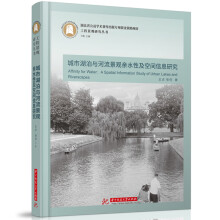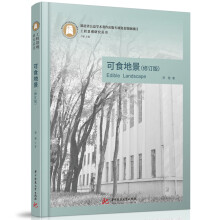第一章 研 究 综 述
1.1 研 究 背 景
1.1.1 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飞速发展,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大国,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但我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其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状况关系着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至2016年,中国农民工规模已经达到2.8亿人 。另一组数据同样引人注目,2016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了7.93亿,城镇化率达到了57.4%,该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是根据居住地进行核实的。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统计,我国2016年的城镇化率是41.2%。造成这种差距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即“半城镇化”现象。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均强调,要提高城镇化质量。城市化不简单是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和城市用地面积的扩张,而且要在社会保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新型城镇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主题,以农民的市民化为本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市民化,市民化不单单是空间的转移、户口的转移,更是城市身份的认同,生活方式的转变。已经有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较低。以深圳为例,2008年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留城比例仅为17%(表1-1),2012年穗深莞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为34.6%(张丽艳和陈余婷,2012),这对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提出了新的挑战。
1.1.2 农民工规模增长放缓及分化
1. 农民工规模巨大但增长放缓
农民工数量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百万人增长到2014年的27 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 821万人,本地农民工10 574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3 243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3578万人 。过去几年虽然中国农民工总体规模在持续增长,但增幅在不断下降(图1-1)。
表1-1 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的未来打算的交叉列联分析表
数据来源:“外来务工人员调查问卷”—2008年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图1-1 2010~2014年全国农民工规模增长速度
2. 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农民工以男性为主,2014年男性农民工比例为67%,外出农民工中男性比例更高,达到69%。随着农民工增速的放缓,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30岁以下的农民工(青年农民工)比例在持续下降,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例在不断增长,31~40岁的农民工比例相对比较稳定(表1-2)。此外,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外出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提高更为显著。高中(包括中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23.8%,比2013年提高1%。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包括中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26%,比2013年提高1.6%(表1-3)。2014年外出农民工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总数的28.3%,自2010年以来,该比例在持续下降;租赁住房的占总数的36.9%,该比例处于上升中;在务工地自购房的农民工达到了总数的1.0%(表1-4)。
表1-2 农民工年龄结构现状及变化 (单位:%)
表1-3 农民工文化程度现状及变化 (单位:%)
3. 农民工的分化和诉求
随着时代发展,老一代农民工已在城市工作长达10年以上甚至20年之久,部分老一代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发展已经在城市获取了较高的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底层的务工者转变为专业技术型和投资经营型的城市新移民,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向上流动。伴随着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其居住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许多农民工不再满足暂居城市,随着居住时间的不断延长,倾向于举家迁移。新一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农民工群体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分化(高春燕,2007)。农民工可划分为有一定生产资本并雇佣他人的经营者、拥有少量资本但自我雇用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务工者(周大鸣和杨小柳,2014)。当前,农民工队伍内有4种群体:一是基本融入城市,并打算留在城市的农民工;二是虽然长期居住在城市,但未打算留在城市的农民工;三是来城市打工时间较短,但已脱离农业活动的农民工;四是农闲时在城市务工,农忙时则回家务农的农民工。农民工内部不同群体的划分,也表现出权利诉求的差异性。
1.1.3 人本主义思潮下农民工聚居区研究的兴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社会与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西方地理学者更加关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移民群体日益壮大,移民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地理学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地理学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聚居区方面,西方国家对移民聚居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美国“芝加哥学派”,随后经历了同化主义、多元主义、异质本地化和跨国主义研究思潮,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相对于跨国移民而言,中国规模*大也*受关注的移民群体为跨地域的农民工。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城市,由于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网络、文化因素、地方认同、城市发展及政策制度等多种影响因素,形成了具有社会标识和文化符号的农民工聚居区。农民工聚居区于1989年第一次在媒体上出现了相关报道,不仅是政府、社会和民众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学者们也陆续展开对农民工聚居区的研究,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和扩展,农民工聚居区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1.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1.2.1 相关概念
1. 农民工
农民工 这一概念*早由社会学家张雨林(1984)提出是中国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与传统户籍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宗成峰和朱启臻,2007)。自我国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实行以来,部分个体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工人,但他们拥有在农村的承包土地,这部分人即是农民工(刘秀英和孟艳春,2004)。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乡镇企业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由此“农民工”*初所指进入乡镇企业的农民;后来又随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为了获得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周其仁,1997),因此“农民工”指代的群体发生了变化,特指外出就业、进城务工的群体,其生活重心已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身份仍是农民(王琳琳和冯继康,2005)。还有学者认为农民工主要指户籍身份为农村户口、在农村有承包土地,进城后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韩长赋,2006;李培林和李炜,2007),但有不少农民工到达城市之后从事个体或者私营活动,而并非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
2006年1月31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第一次在中央层面并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文件中写入了“农民工”这个概念 。所指农民工包括两大来源:一部分来源于在家乡及周边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工,即“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另一部分则来源于离开家乡,跨越一定层级行政范围到外地去打工的农民工,也称“外出农民工”或“流动民工”。根据国家农民工监测的统计口径,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主要差别在于农民工从事非农活动的空间范围,如果在本乡镇内,称为本地农民工,若在本乡镇地域以外,则属于外出农民工的范畴。
对上述观点归纳后,本书认为农民工是指常年在城镇生活和工作,但户籍仍为农村户口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强调户籍,“工”强调职业。农民工的本质属性包括以下3个层面。①第一个层面是制度身份。尽管农民工从事的活动不再是农业,而是第二、第三产业,但在户籍身份上还是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还是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身份差别。②第二个层面是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从事的主要是非农职业,即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为主要职业,收入相应地也主要来自非农业生产活动。③第三个层面是地域变化。他们大多来自广大农村包括山区等,到城镇去打工谋生。
2. 农民工聚居区
国内现有文献对农民工聚居区的界定主要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进行分析。定性界定主要包括空间分布、形成方式、居民构成及农民工比例 等指标。聚居区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以房屋租赁为首位住房模式、以城乡接合部为主要区位选择的集中居住区(吴晓,2003)。有学者认为农民工聚居区是具有一定规模、相对稳定的以农民工为主要居住群体的居住小区或居民点(罗仁朝和王德,2008)。还有学者从研究单元、农民工数量和本地户籍人口数量的对比来界定农民工聚居区,认为农民工聚居区是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农民工规模一般超过户籍人口规模的农民工集中住地(冯晓英,2010)。
尽管农民工的住房来源包括租赁、集体宿舍、自购等多种形式,但要形成具有一定社会空间特征的农民工聚居区,需具备四大条件:①居民身份,农民工聚居区的居民是以农民工为主体居民;②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工总量,这是构成聚居区的基础;③农民工占总人口的比例较高,表现出农民工高比例的集聚;④相对稳定的聚集状态,如此才有一定的持续性(罗仁朝和王德,2009)。结合前人研究,本书根据研究需求认为农民工聚居区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农民工群体有固定住处(包括租赁、集体宿舍、自购等)、在人口规模上占据了相当比例(大于50%)的相对稳定的居住区。
3. 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Emile Durkheim在19世纪末提出,20世纪50年代之后,学者们开始广泛使用社会空间这个概念。学界关于“社会空间”有众多解释和界定,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