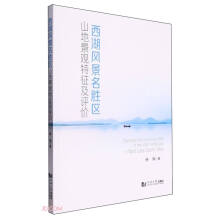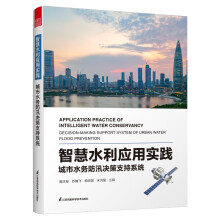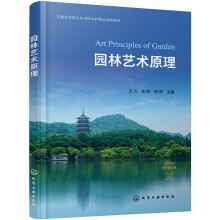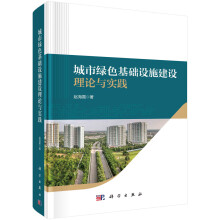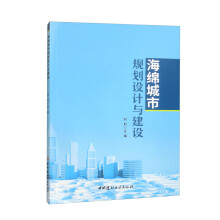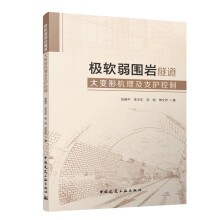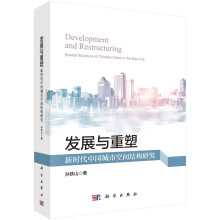第一章 创新型街区的内涵
2014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斯 卡兹(Bruce Katz)发表了研究报告《创新区的崛起:美国创新的新地理》,基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创新企业与人才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居住的现象和由此形成的特定地理空间组织,首次在文字上明确形成了“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的概念。在这份报告发表前后,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类型的创新区、创新型街区等展开了广泛研究。
第一节 创新型街区产生的背景
一、城市空间格局转变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内在机制在于形态需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功能要求,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将破坏城市原有功能与形态的适应性关系,导致城市空间形态转变。在工业经济时代,追求规模和自然资源占用的批量生产方式导致城市空间不断向郊区扩张与蔓延。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新经济与新产业不断成长,城市空间形态受到生产系统复杂化、社会分工精细化、消费产品个性化的影响,呈现向城市中心区收缩回归的趋势,并且日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城市内部,传统街区被升级改造为结构紧凑、环境宜人、功能混合的新型城市空间组织,具备了创新型街区的雏形。
(一)知识经济引发城市空间结构向高密度转变
在创新驱动下,互联网等信息流促使知识型城市的企业生产、居民就业、公共设施配置发生改变,进而引起对城市的产业、社会空间以及形态结构进行再组织。1990年后,发达国家的都市区涌现出大量新型要素及功能空间,承载居住生活、商务办公、文化休闲等不同功能的城市空间都在向高密度、混合集聚的方向转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便携式电脑和无线互联网的出现带动了个人智能手机和电子邮件服务的使用,人们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界线更为弱化,无论企业如何努力在远郊区的办公楼周边增加各种商业设施,员工还是对每天必须远距离通勤去工作缺乏热情,因为这里没有真正的城市生活。因此,城市中心区逐渐成为创新型企业区位布局的新选择。当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关键因素后,企业更加注重社交活动对创新的刺激,开始争取创造能促进创新的多样性的办公空间,如开放楼层规划、灵活空间和“非领地型”办公规划等,并建立规范以提高部门间的合作效率、改善创造性的工作环境。知识型员工被较短的通勤时间、更好的配套服务设施和步行街区所吸引。从纽约、旧金山和波士顿等城市中心区小户型商品房的热销也可以看出,许多城市居民也愿意为获得更完善和多样性的便利设施及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住宅面积[1]。
以知识型社区、电子村落、数字媒体社区等为代表的新型居住空间创造出了全新的“职住”与“生产生活”模式。它们更加强调“非例会式办公”,注重个性化、家庭情感、远程互动和自主管理[2]。1990年以来,全美远程办公族的数量持续增加,至2001年已达约3000万人;从1997年到2005年,伦敦 SOHO族(即居家办公的就业者)占劳动力的比例从4%提高到8%,达到240万人,成为推动新型居住空间形成的关键[3]。新型居住空间强调高知和智力群体与多功能社区的就近适配,“校园+研发+社区”的合伙关系在全美逐步得到认可,仅1994~2002年就有143家高等教育机构实现与所在社区融合发展[1]。在北欧,传媒、设计等个性化、创造性行业融合技术研发和团体机构形成一批创新社区,如2000年兴起的哥本哈根奥雷斯塔德社区(Orestad Nord)等[3]。
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商务、保险等行业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就业人数持续上升,使得传统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中的部分基础商务职能相继外迁,高端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向城市中心区集聚,需要面对面交流的“管理决策、信息咨询、金融法律”等功能在中央商务区重组,形成新的市中心总部经济区。2007年,全美2/3的顶尖会计师事务所、3/5的大咨询公司集聚纽约曼哈顿,4.4%的世界500强企业将总部设在纽约市中心;2008年,伦敦金融城内集聚有近2000家金融机构、500余家国际银行和近200家外国证券交易中心[4,5]。与此同时,共享经济越来越广泛地渗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具有共享功能的高品质公共办公空间日益成为生产和容纳不同创新创意产品与服务的“容器”,充当了城市内部新型产业空间的角色。人们在共享空间供给或享受丰富的个性化服务,并且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利用同一空间的不同功能,显示出这类空间的高度混合与动态性。城市中心成熟街区的人际交往紧密、商业活动频繁、社会互信度高,正是推行共享活动的理想场所,逐渐成为新型办公空间的集聚地。
受到人本主义思潮、能源危机、健康意识以及迅速膨胀的商业设施带来的内部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众多郊区购物中心的发展速度锐降,人们对更强调内外空间的开放渗透、注重个人主观感受和消费环境品质的城市商业步行街的重视度逐步提高。在此背景下,来源于美国的 BLOCK街区①开始兴起,将人居、商业、生活休闲配套紧密交融,力争营造一种悠闲、活力和友善的人文氛围。这种以街区形态出现的新型城市空间,在适宜的尺度上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提供了多元、丰富的商业及休闲配套服务。街区中自然与人文景观并存,主要设置一些温馨而亲切的小型零售商店和情调餐厅、咖啡座及静酒吧,整体上呈现开放式布局,是一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配套商业群落,更能够与周围人群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二)旧城更新带动创新要素向城市中心区集聚
20世纪早期和中期,由于人们对健康和环境愈发重视及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工业被推到城市之外,人口与就业开始迁向郊区,出现所谓的产业空心化和居住郊区化现象,给许多城市中心区留下废弃的铁路、工厂和衰败的城市社区。随着郊区生活品质的相对下降,人们重新焕发对城市中心区生活的向往,城市中心区和多功能商务区所拥有的“1平方英里效应”②在相对小的地理面积上带来巨大价值输出,进一步促成了1990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广泛存在的主城复兴。那些原先遗留的“城市疤痕”空间大、成本低,成为城市复兴的机遇区,通过地理空间上的功能整合与结构重组将分散在郊区的人口与就业重新带回城市心腹地带。例如,伦敦格林尼治半岛改造工程中,首先就通过调整煤气工厂土地功能,将传统工业空间转化为多功能生活空间,培育出具有较高价值的文化休闲中心,进而推动了该地区的新一轮开发[6]。东京市新宿区采用“小型街区+高容积率单栋建筑”的模式在单一功能的商业中心植入大量商务办公空间,不断强化其国际商务职能。与此同时,航空、铁路枢纽、高速公路交通体系的愈发完善也助推了发达国家废弃和未利用城市地区的盘活与振兴。截至2007年,东京市各类轨道交通通车里程达到845千米,是1980年的2倍有余,二十余年人口密度梯度变化与轨道交通向郊区不断延伸形成密切的关联[7]。
此外,以2008年前后的经济衰退为触发点,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意识到打造拥有丰富的创新创业活动的城市将更有利于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机会,进而可以提升经济弹性和区域经济转型的潜力,因此开始有计划地在城市内部推动创新型街区的建设。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初创和中小企业入驻城市中心区创新型街区的成本下降、收益上升,地方政府的综合收益也得到提高[1],从而使政府有能力继续投入当地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住宅和商业进一步增加,吸引更多研究型大学、医疗综合体以及创新创意公司在城市中心区进一步集聚。美国大都市区的城市更新与改造,更加重视创新空间在促进传统建筑与区域改造中的积极作用。例如,在纽约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的区域更新过程中,开发方不仅从硬件上对区域内的建筑与周边环境进行了改善,还十分注重区域创新功能的注入和创新空间的建设,将其中面积*大的77号大厦逐渐转化成一个集聚了众多生物医药、高科技以及小微型制造业企业的中心区。波士顿市政府也针对其过去多年发展缓慢的问题,提出打造集创业工作、居家生活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城市社区,不仅对区域内的公共空间和老旧产业空间进行改造,还策划了一系列会谈、研讨、展销、创业交流等活动,激发市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
二、创新活动的进化引发空间形态转变
随着人类科技革命的迅猛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由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与发展而催生的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模式成为主导,更加强调以用户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理念,用户不再只是创新成果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可以直接参与创新的过程,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成为新时代创新活动的典型特征。在企业、研发机构、高校、用户等主体之间的开放创新互动过程中,创新空间正经历原有空间载体和界线的重构。
(一)创新活动对地理邻近和空间品质提出更高要求
过去,针对创新的分工相对较少,为了实现对知识的高度保密,企业更加倾向于利用本公司的资源和技术进行产品的研发。考虑到技术系统复杂、市场竞争激烈、成本风险增加及研发联盟形成等因素,高端研发体系对外部支持力量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信息流动的自由化、高等教育的广泛普及加速了知识生产的扁平化,进一步松动了封闭式的知识壁垒[8]。基于此,企业将竞争优势转向更有效地利用他人的创新成果,通过建立外部渠道、整合外部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和效益,各创新主体与创新要素之间通过强弱联系建立正式与非正式合作,形成了紧密的创新网络,提高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弹性和经济转型潜力[9]。创新环境理论认为,开放的创新环境可以实现共同学习和信息共享,弥补创新、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而空间邻近性、非预见性的面对面交流等都将促进这种开放式创新[10],并扩展成新的产业,进而改变办公空间的设计,重塑建筑间的关系,进而逐渐延伸到城区尺度上,使创新的过程在公共和私人领域更具渗透性。
在此背景下,科技创新过程产生了大量外包的研发、生产、服务等多个协同创新环节。这些环节一般灵活地选择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和方式进行布局。城市中心区具备的创新服务供给和创新资源配套优势,吸引了大量创新功能不断聚合,并建立起具有较强专业化服务能力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其中,一些创新环节倾向于围绕完整的生产配套体系和生活配套体系进行布局。以科创孵化器、联合办公平台等为代表的要素服务指向型空间,就是利用城市中心区完善的生产服务业体系形成的创新集群。一些小微科创企业则利用城市中相对廉价的闲置写字楼、工业用地、仓储用地等存量空间进行布局,形成了独特的科创街区和科技社区。为满足创新集群需要,当地传统商业街区、生活社区和建筑单体的业态与功能也随之加快转化。
当前,企业与周边环境之间的界线更加模糊,创新能够在多个企业之间高效地交流和移动。在高度复杂的知识密集型行业,从内部研发实验室到“多渠道研发路径”的转型成为趋势,学术中心、合作对象、竞争者、顾客、风险资本及创业公司等各种活动者,更加促进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集聚,并影响到企业和配套组织的空间布局,进而走向高科技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凯伦 温特劳布(Karen Weintraub)对波士顿剑桥市的一些医药公司的考察表明,近年来多家医药公司开始将其研发部门布局于领先生物技术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主要研究型大学附近,以便更好地接受知识外溢和网络合作[11]。
对于创新活动而言,知识被认为只能通过人际接触和跨企业流动进行有效的传递,因此会被地理性地限制在区域内[12]。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并没有使知识工作者在任何他们想要工作的地方工作。相反,知识型产业变得更加聚集在位于特定地点的大学、研究机构周边。成功的高科技集群案例研究表明,在传递隐性专业知识过程中,基于共同的目标和工作分享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互动十分重要[13,14]。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将交流行为作为启发创新的*重要资源。在交流中,人们可以发现新的重要信息来源、获得资源或者进入新的市场、强化部门间的合作等,而传统办公建筑中的接待室和会议室已经远不能满足现代创新对于交流的需求[15],一批新型创新空间应运而生。例如,在谷歌公司(Google)内部,建筑师就采用了可变平面布局以满足创新的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