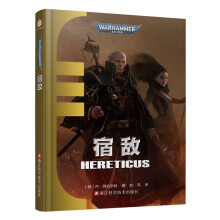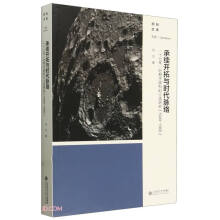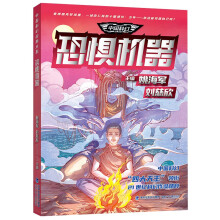失语者
除非我们把语言减少到七个字,我们将永不会互相了解。
——纪伯伦《沙与沫》
在我生日那天,全球三十万多人同时失去了语言能力。
这场盛大的阉割,没有任何征兆,犹如一场骤雨降临。在这一天失去语言的人,性别、肤色、种族完全随机,除了年龄都在二十一岁以内,其他没有任何规律。唯一能让人产生一丝联想的,就是不久前那场异常天象了,在亚欧大陆部分领土上空,不少人看见了带着彩虹般色彩的光束从空中垂直落下,持续时间只有几秒,有人以为自己出现了瞬时幻觉,但有照片证明这圣光是真实降临的。不过后来,普遍说法是特殊气象产生后的大气折射。
可那之后,语言能力就从少数年轻人类手中溜走,包括我。我们能听、能看、能思维和行动,只是不能说,仅此而已。至于为什么发生在我生日那天,不过是无数巧合中最不起眼的一个罢了。
关于我们语言能力的失去,是退化还是进化,究竟是一份礼物,或是全然未知的阴谋,短时间内没有定论。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布消息,而对于此事的猜测,各路媒体则将想象力变成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分析,从基因缺陷到哈米吉多顿①的末日预言,应有尽有。
我们的失去,俨然成了他们的狂欢。
在无数好奇和质疑的声音中,我们始终保持缄默。直到我们明白,失去语言,是一场人类跨越与自身鸿沟的仪式的开始。后来,我们把那一天叫作“失语节”,而在其他人眼中,我们暂时成了异类,是神秘的“失语者”。
1
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对“不能说”感到恐惧。
我第一次开口说话是在五岁,在此之前,我被当成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女孩,爸爸也这么认为。算命先生说,我以后会很好命,只是老天把这部分功能暂时遮蔽,迟早会还给我,妈妈笃信这一点,但爸爸没有。他还想再要一个正常的弟弟,妈妈没同意。
爸爸离开那天,小雨,一件黑色风衣将他包裹住,我抱着他买的洋娃娃,静静地看他的背影。他提起行李箱回过头,欲言又止。我望着他步入雨帘,那件黑色风衣像一块黑色石碑,堵在我的喉腔,雨水倾盆而下,石碑仿佛慢慢融化。
三天后,又是一个雨天,我对妈妈说了第一句话——“妈妈,他走了。”她哭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哭。
为什么在最需要语言的时候,语言会失效?不能说和不敢说,都会让我承受失去的痛苦。于是,我的身体机能启动了一种“负反馈调节”,上高中前,我拼命学习好几门外语,还有古汉语和方言,我不断参加演讲比赛、辩论,到学习小组和各种人交流,我努力地说啊说啊,仿佛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真实存在。
事情发生的几个小时前,我在家里听英语教材。那天是我十七岁生日,妈妈答应我会早点回家陪我吃蛋糕,还说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午睡过后,我发觉喉咙一阵干涩,灌了一大瓶水才好些,就在我准备跟柠檬聊两句时才意识到,我的声带彻底失去了作用。
我失去了在我看来最宝贵的东西,而且是第二次。
我不停尝试,张开嘴对着空气大喊,没有一丁点声音,周围仿佛成了介质消失的真空。柠檬是只猫,当它看到我因惊惶而扭曲的表情时,扬起尾巴在我脚边盘旋,代替妈妈的安抚。她早早把家里的全息墙面调成了海滩的模拟成像,我呆呆地望着远处翻滚的海浪,似乎有海风拂过面颊,惶恐无助的眼泪乘着那阵风飞到天上,随后便是一阵天旋地转。
妈妈在傍晚回到家,爸爸随后也到了。每当我赢得比赛都会拍照发给他,我可以无数次证明给他看,他当初的否定是多么错误。然而这一次,我还是输了。还有杨一川,同妈妈一起前来,我喜欢的男生。我以为是个秘密,看来妈妈早就读懂我有意无意提起他时脸上的笑容。
那一刻,我汗湿的头发贴在额头,嘴唇微微开合,努力挤出笑容,看着他,然后低头沉默。沉默了不知多久,他端着蛋糕站在我面前,期待我说点什么,然而什么也没有。他的表情慢慢凝固,疑惑、失望,说了旬抱歉然后离开。爸爸妈妈的质问像是来自远方的回音,在我耳边萦绕、消散,最后被我们之间巨大的鸿沟吞噬。
我哭了整整一晚,不带一点声音。
妈妈比我坚强,像当初同意爸爸离开一样。
我停下了所有语言课程的学习,不敢去上学,更不敢独自离开家门。妈妈带我去多家医院治疗,检查结果很一致,没有任何异常,声带没有受损,脑部神经及感官功能正常。
P1-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