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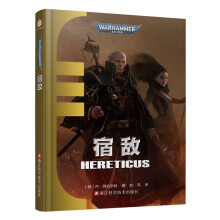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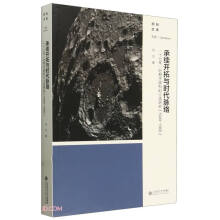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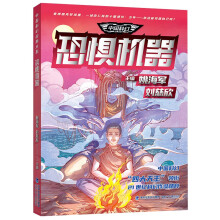
哑蝉:科幻能永远年轻的秘诀是,永远有年轻的科幻创作者全情投入。借这句话推荐这本“星云”,带你沉浸式体验年轻一代科幻创作者卓绝的想象力和蓬勃的创造力。
瓦泥十:喜欢《见字如面》和《新贵》这两篇。王元老师笔力很深,寥寥数语就可以勾勒出悼亡妻者仿佛一块裂而不碎的玻璃般的心境:表面平静无波,内心压抑的深切哀悼和思念却渗透在每一个角落。灵船和仿生白鹤的设定也很亮眼,被画成了封面。
《新贵》典型赛博朋克故事里科技践踏生命的警醒性、细致的心理描画,以及虚无泥潭中真挚人性的闪光,挺触动人的。
l 推荐语/媒体评论:
坐在烛台上
我是一只花圈
想着另一只花圈
不知道何时献上
不知道怎样安放
——海子《爱情诗集》
∞
史婧:
见字如面。
好久不给你写信,你在那边一切都好吧?
我都好,猫也很好,不用挂念……
2
他们劝我节哀顺变。
还好吧,我并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哭天抢地和捶胸顿足,我很平静。
人固有一死。她去了天堂。不必拿这些敷衍的安慰话搪塞我。很难说清楚这种感受,更多的是空白,提笔忘言——我曾无数次面对一张白纸,静默整夜;碎裂的想法在空中飘浮,思绪像含羞草的叶瓣,碰触只会制造闪躲和闭合,不如远观。
此刻,我坐在灵船上,端详水晶棺中的妻,她神情安详,睡着一般。过去我夜半惊醒,看到床头灯洒下的橘黄色之中就是这样一张不动声色的脸。她穿着白色长裙,双手叠放在腹部,掌心压着一本诗集,我的诗集。她的父母和亲朋环绕在棺椁周围。仿生白鹤不时传来阵阵清唳,为轻缓的背景乐和声。我擅自做主,把哀乐替换成一首古老的流行歌曲《稻草人》,这是我跟妻甜蜜爱情的见证。
透过舷窗眺望,飘浮在空中的墨城A-3 区灵堂已显露轮廓。那将是她的归宿。灵堂风格复古,跟灵船一脉相承。灵船外形复刻自一艘明朝官船,顶层覆盖琉璃瓦,两侧各有一双竹竿与帆布制成的机翼,当然,只是用来调节方向,真正的动力装置埋藏在船底控制室。这是一艘名副其实的飞船,飞在空中的船。至于灵堂,更像一座中式堡垒,一圈圈的房屋叠凑,凸出的屋檐由斗拱支撑,雕梁画栋,器宇轩昂;四周各有一座玲珑宝塔,寄存骨灰盒。乍一看,不像灵堂,倒像天宫。
如今,死去的人都到了天上,这再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修辞。
我其实挺排斥这种场面,不管是婚礼还是葬礼,在我看来,都有些形式大于内容,那些被传统观念辐射的参与者大多抱着应付差事的心态,婚礼和葬礼只对一两个人的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我真想把他们赶下灵船,一脚一个踢到空中,包括她的父母,我不愿和任何人分享她的最后一程。大部分来宾甚至不如司仪投入——他一袭牧师黑袍,与中式丧葬氛围格格不入。或许他真的是位牧师,主持完葬礼就要去教堂聆听告解。我不信这套,不管祈祷还是超度,都不能让妻回生。
死亡不是为逝去的人准备,而是为活着的人张罗。
灵船泊入港口,白鹤悬停半空,铺出一条肃穆甬路。送葬者跟随司仪上岸,步入告别大厅。工作人员把水晶棺推到厅前,在周围布满绢花,妻的全息影像从棺中浮出,宛如魂灵出窍。她平时不苟言笑,我翻遍云端,才拾得几帧欢乐的动图。
她笑得真美,我的心都要化了。我们被要求围绕遗体逆时针转三圈,之后垂首聆听司仪的葬词。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告别史婧女士,她是孝顺的女儿,是贤惠的妻子……”
瞻仰遗容,最后一次看她,我咬紫了嘴唇。
送别时刻到了。
我常常用两行俳句自勉:随时准备面对死亡,只要活着就感谢上苍。我现在仍然要感谢上苍,死去的人是她,若不然,她该有多恨活着。唉,我有些想当然,如果躺在水晶棺里面的是我,她也会顺着过去的轨迹一如既往地向前滑行吧。
水晶棺落入熔炉,换回一抔温热的骨灰。灵船压抑的氛围终于被引爆,人群像一朵窝藏惊雷的乌云,响起此起彼伏的哭声。岳母泪如雨下,悲痛欲绝。岳丈假装沉着,悄悄用手背擦拭眼角。我没有任何反应,那一瞬间,我是死的。酩酊之人一定有过以下体验:从饭店出门,坐车,呕吐,脱衣,上床,自己对这一系列行为都有印象,一觉醒来却无法回溯醉酒经过,一切仿佛一场失重的梦。我当时就是烂醉如泥的酒鬼,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有朦胧的距离,我身处葬礼的中心,却毫无参与感。灵船起飞,白鹤送行,大厅送别,火化成灰,灵堂安息,整个葬礼忽远忽近,我都不知怎么回到家中的。
回到家中,客厅电视墙糊着一张白纸,上面用楷书写着一个“奠”字。不知怎的,看着那一笔一画,一撇一捺,墨色在宣纸上洇开的毛刺,我突然泣不成声。
我以为我很平静,我以为我不难过。
我以为。
3
我其实挺排斥这种场面,诗人都是孤独分子,但黑纸白字写进合同,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宣传。我坐在椅子上,像待价而沽的商品。其中一个环节,读者朗诵诗歌。他们手捧散发新鲜油墨味道的诗集,挑选心仪的几行,或情绪饱满,或冷静平淡。作为诗集的创作者,我也被邀请到舞台中央。我有些胆怯,他们的目光鼓励我,别不好意思。我深吸一口气,微微闭上眼睛,只能感受到模糊的光,无法视物。光晕之中,我仿佛看见史婧,她像往常一样慵懒地窝在沙发上,手握一支铅笔,在纸上沙沙地计算,或者补数独游戏的空。猫在沙发靠背上轻巧地踱步,走到尽头,拱起脊背,笼出一个巨大而无声的哈欠。
我曾和你在一起
在黄昏中坐过
在黄色麦田的黄昏
在春天的黄昏
我该对你说些什么
我声如蚊蚋,小心翼翼,如初次行窃的小偷。这是我为史婧写的第一首诗,记录我们初次相遇的傍晚。她瞥了一眼就扔在茶几上,继续在数字的海洋里徜徉。
我承认自作多情,从这首诗开头,牵出整本诗集。我跟编辑沟通,于扉页印刷“送给我的妻”。出版之后,我把第一时间收到的样书手写To 签送她。她只是礼貌地说了一声“谢谢”,就把书塞进书架,和一堆与数学以及数学人物相关的读物混在一起。我想她从未翻过,我把那本书与她的遗体一起火化只是出于个人情感需求。
我知道,她不会共鸣,以前不会,没有以后。
签售简单一点,这年头看实体书的人不多,诗歌爱好者更是凤毛麟角,排队的读者很快散去。诗集能够再版已是奇迹,我不期待奇迹中的奇迹。
发布会结束,我如释重负。
我在书店随便转转,凭借书封和书名遴选入眼的新书,以貌取人。
“你好。”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男人走到我面前,递过一本诗集,我的诗集,“你是罗凯?”
“你好。”我接过诗集,从口袋里掏出钢笔,随手一甩,拧掉笔帽,签下名字,“需
要再写点别的吗?或者致谁?”
“我能跟你谈谈吗?”
“写这句?”
“我是警察。”
书店就有咖啡厅,据说饮品营业额远远高于图书销售。我们挑了一个角落坐定,两杯热气腾腾的拿铁将我们隔开。我轻轻地吹散杯口氤氲的水汽,等他开口。
他并不着急,气定神闲地翻着诗集,不时发出一些短促的点评,比如“写得不错”,比如“看不明白”。没一会儿,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生抱着一摞漫画在他旁边坐下。
他戴棒球帽,穿格子衫、牛仔裤和帆布鞋。一摞书堆在桌上,顶住他的下巴,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他的脑袋仿佛刚从书中出土。他们简单地打了一个招呼,我听见男人抱怨“多大了还看漫画”,男生没有反驳,只是附赠一个白眼,抽出一本漫画,一头扎进去。
“这是我的同事,隶属网络安全部,来协助办案。”男人合上书说道。我几乎误会他们是父子。他端起咖啡,随意地啜饮一口,“你听说过‘质数的孤独’吗?”
“嗯。”这是史婧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我们在一起这些年,我每季度都要陪她重温一遍。她常常说,我们两个人就是两个质数。在我们各自的生命中,她的1是数学,我的1 是诗歌,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不能再被其他事物整除;所以我们没要孩子,担心他(她)会成为搅乱我们世界的公约数。她是我的保护色,我是她的皮肤衣。我们只是需要婚姻的框架来规避他人多余的热心和过分的关怀;我们只是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相安无事的两个房客。
“简单说吧,我们收到情报称,他们要搞一个大动作。”
“等等,电影里没有类似的剧情吧?”
“电影?”他疑惑地看我一眼,“我说的是恐怖组织。”
“那没听说过。”
“不会吧?你老婆可是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很久没人在我面前提起史婧,我有些恍惚,好像她还活着,只是出了趟远门。只要我在门口坚持眺望,就能等到她由远及近的影子,影子会从地上袅袅升起,化为人形,对我张开双臂,开口说话……见我没反应,他继续说道:“这个恐怖组织,没有一枪一炮,没有非法集会,但是他们造成的恐慌和破坏,是其他恐怖组织相加也无法比拟的。”
“你一定搞错了。”我摇摇头,“我妻子已经去世一年了。”
“时间刚刚好,他们的计划正是一年前启动的,马上就要收网了。”
“但这跟她有什么关系?”一个因意外去世的人,能对这个世界造成什么恐慌和破坏?
“这可说不准。”他有些含糊其词,“你最近有没有遇见什么怪事?打个比方
啊,不一定准确,就是,怎么说呢,灵异事件——”看漫画的少年此时抬头,颇为不屑(抑或不满)地望向男子,后者劝他,“你先别插嘴,回头有你发挥的机会。”少
年叹一口气,缩回书中。
我呼吸急促,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害怕错过从他嘴里溜出的每一个字,虽然他支吾了一堆毫无实义的虚词。这种感觉就像溺水之人从水底向上看,白蒙蒙的光亮中伸出一只手;抓住那只手,不顾一切!
“这么说吧,你有没有见过鬼?”他兜了一圈,抛出这个让我哭笑不得的问题。“我是无神论者。”我相信万物有灵,但我仍然是一个无神论者。所谓“灵”只是诗意的寄托,比如一朵花含羞,一株草叹气,一朵云飘过诉说一场雨,一只蚂蚁在我掌心纹路走迷宫……一个字追逐一个字,疏离另一个字,结行成章,就有了灵魂。我不相信人死后的灵魂,虽然我不止一次做过类似假设,在史婧去世第七天夜里点一根白蜡,彻夜不眠。我什么都没有等到,什么都没有看见,只有入室的风伙同烛火摇曳我的孤独。看啊,它们说,一个伤心者。什么叫形单影只,这就是形单影只。我在稿纸铺张一万个字的忧愁,也没这个成语戳心。
“我也是。我们谈论的是科学,不是迷信。如果你遇见任何离奇事件,打给我。”他掏出手机,拇指按住屏幕向上一滑,发射一张虚拟卡片,我捏住,塞进手机。
高赛,墨城市第二刑侦大队副队长。照片比他本人更加沧桑,显然没有使用美颜插件。
“高赛?”
“对,他叫小杰。”高赛指了指少年,少年向我颔首示意。
“她还活着?”
“我可没这么说。”高赛说,“不过,的确有人在玩濒死游戏时看见她。你听说过那种游戏吗?真他妈变态,用绳索勒紧自己的脖子,就跟寻求刺激的性瘾者似的,体验窒息的快感。这年头什么人都有,不是吗?你还写诗呢!”
“你们怎么确定是她?”我穿过他连篇的废话,站起来,向前探身,差点抵住他的鼻尖。
“他,那个濒死体验者,捡到一本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书。喏,”他用下巴一点,指向桌面的诗集,“就是这本。上面还有你写的寄语:To 史婧,你是我心里的一首诗。没错吧?”
见字如面 1
星云会客厅 “把石头还给石头”——王元专访 54
卡西米尔之墓 63
星云会客厅 一朵只属于科幻的火花——氦五专访105
明天就出发 111
新 贵 135
温馨提示:请使用沧州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