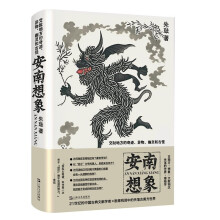《冬草无咎:我的阆苑旧事》:
四合院里的人,都是丝厂职工家属,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关系也有亲疏之别,和我家关系最好的应该是鲜家,这家的男主人貌陋身短,颇受了不少讥诮,妻子刘氏却是人才出众,这两人为何会凑在一块,当中的因由要另出一本传记的。
这鲜家的崽子比我小一岁,同在丝厂的附属幼儿园念书,我上中班他上小班,我上大班他上中班。原本我们都是由各自父母接送的,后来有一阵子不知怎的没人接送了,刘阿姨让我和她家崽子一起上学顺便照应一下,但是第一天我就把小弟弟弄丢了,两口子火急火燎把儿子找回来,后来再没人让我干这差事。
我家原本没有厨房,只在过道里放了一只蜂窝煤炉子供烹制食物之用,过道极窄,再放这样一件家什其实很不方便。四合院里除了马爷爷和江婆婆家,其他人上厕所都要经过此处,非但有碍观瞻,而且于理也不合。如今物是人非,那过道比记忆中更觉压抑逼仄,但我于此仍有温馨的回忆。记得大约是我五岁光景,有一次外婆从乡下来看望女儿及外孙,背了许多粮油菜蔬,我们一起上街买了新衣,还买了一只绝大的火腿。回家后母亲立刻在煤炉上烧了一锅滚水,将火腿置于手中削片,片片皆入水中,那火腿用了约有三分之一的量,佐以番茄豆芽之属,风味殊胜,却不知是什么牌子,此后再没有吃过。
后来鲜家拿到新的分房名额,而且是楼房,大家都非常羡慕。我父亲那时很出风头,而鲜叔叔的工作能力据说是垫底的,却后来居上,令人不解。他们走后,厨房立刻被我家和另外一家瓜分了,中间以水泥墙隔离。
新厨房有两平方米不到的面积,不但有了正经做饭的地方,甚至还有余裕装了一间小小的洗浴室,比起以前那只全家共用的大澡盆,那真是不可信的奢侈。
如果能再有一个独立厕所的话,那么我在四合院的生活条件就能达到一个质的飞跃了。
可也只能做做梦。
院子里垒着一个公用的土厕所,男女分离,我估计余华的《兄弟》中那位李光头偷窥女人屁股的地点,就和这种很类似。因为是旱厕,卫生情况好不了,常年散发阵阵恶臭,两个小小蹲位叫人触目惊心。院子里的江婆婆家,很不幸紧挨着这厕所,因她当年也是从乡下嫁入城的,非常勤俭持家,弄来一只小小鸡笼放在门口,常年养着两三只鸡,平时下蛋,过年吃肉,那两三只鸡蔫头耷脑,也生得一副倒霉相。我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暗道一声可怜,毕竟也是昴日星官的原型,就这么潦草地过完自己的一生,哪里比得上乡下的鸡崽满山跑,虽然都免不了过年挨一刀,也毕竟潇洒快乐过。
由于鸡粪和厕所的气息浑然一体,我不得不另外思量对抗之法。奈何我幼时思虑极多而行动极蠢,最终决定上厕所时捂住鼻子改用嘴巴呼吸.还自以为得计。也亏得小孩子肾气充足,只要闭眼就一觉睡到大天亮,无须起夜,不然睡得迷迷糊糊起来解手,脚跟没踩稳掉进茅坑里,那可不体面。想起当年,每晚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总要磨磨蹭蹭好一会儿才能入睡,要么睁大眼睛追逐着从门缝里射入的光斑,看它的修短圆缺;要么仔细聆听着天花板上的异响——那是耗子们集体出动的声音,我总觉得它们在操练武艺,一霎儿来,又一霎儿去。风风火火、恍恍惚惚。我十分惧怕老鼠,生怕自己睡觉的时候被咬掉鼻子耳朵,是以喜欢捂着头脸睡觉,即使如此,它们每晚操练的声音仍然声声入耳、巨细靡遗。如今回想,能弄出这么大动静的耗子,一定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体量,而是一个师或一个团。
耗子虽然猖獗,终究个子小,让我吓得夜夜啼哭的,是右边隔壁的大老虎。大老虎每晚嗷呜嗷呜,小朋友我每晚哇哇大哭。母亲还总笑说,不是老虎,是隔壁的赵爷爷打呼噜。我家的右邻正是住着一位体格健壮、声若洪钟的赵爷爷,平时人很和善,看不出和老虎任何相像之处。无数个夜晚,他的呼噜声带着巨大的威慑力,穿透瘦瘠的墙体直击我童稚的耳膜,这样大概三年,我已经能和这呼噜声和平共处,某一天却发现似乎久未听闻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