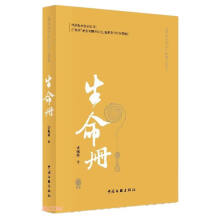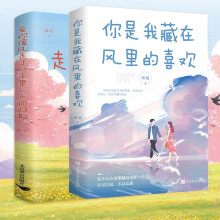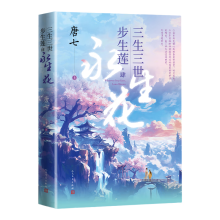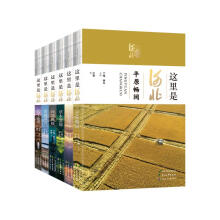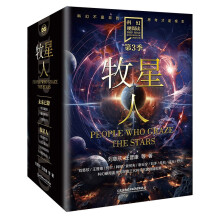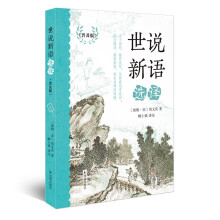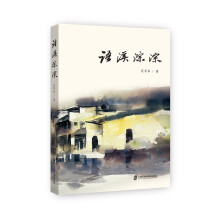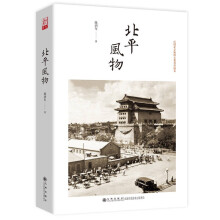《周易》符号在占卜的过程中要针对时间进行判断,要关注时势的变化,同时还要时刻观察时间的延续中,时势所处的阶段,以便对应变对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时空场域是相对静止的。在文本中,相同的符号会随着语境的改变而发生阐释的变化,时过境迁就是语境变化最主要的状况。但无论符号的意义发生何种变化,其终究要依靠人的解释才能有效。所以,人与时间和意义之间具有复杂而密切的联系。
首先,人时刻存在于时空环境之中,没有独立于时间的人,而人也是在时间的推移中完成一生的旅程。人只要生存于世便与时间结下了不解之缘。时间是人对外界的分节,而人也永远是时间中的人。时间对于人来说也只是标注存在的一种特定的符号。中国古代运用十二时辰、六十甲子或者沙漏、香篆等来规定时间,西洋则发明了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分节。人类的世界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的世界,只有分节才能为人所把握,客观事物只有成为符号阐释的对象才能被人类所利用和理解,否则便脱离了意义而只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存在。无论在何种文化境遇之中,时间都是人自身存在的客观因素,任谁也无法逃脱这个宿命。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中有这样一个情景:昆丁看着手表的指针在跳动,感到了时间在分分秒秒中流逝。他不想面对时间的变化,于是故意弄坏了手表,将上面的指针拔了下来。但是,手表的机芯还在继续工作,并且发出嗒嗒的跳动声。①但是,现在手表上已经没有了指针,对于昆丁来讲,他没能阻止时间的前行,而只是使自己失去了对时间符号的分节能力。对于不能把握的意义,他更加无可奈何。因此,时间也是一个由人来界定并赋予意义的符号。时间变化导致的意义变化,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符号意义的改变转而影响了其他符号的意义。人生活的时空只是一个庞大的符号场域,在这个场域中集合了各种符号,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系统。部分符号产生变化必然导致整个系统的内部调整,从而才能保证其正常运作。这符合皮亚杰对系统特征的描述,即体现了系统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周易》之所以可以做到预测吉凶,判定事物发展的趋势,也是以承认现象世界的整体符号场域为前提的。正因如此,《周易》才能把握其中符号变化的规律。
人在所处的环境场域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符号的交流和对外界的阐释。在符号的阐释中,人认识了世界,同时也确立了自我的存在。“主体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主体的意向性在与世界碰撞时,从事物相关的‘可理解性’中释放出意义。意义是事物为我的‘存在于世’作的贡献,我之所以能栖居在这世界上,正是因为世界对迎着我的意向性产生的持续而充沛的意义之流。”②因此,意义其实是与人同在的。符号是被认为携带了意义的感知,然而没有人的阐释,意义也就不存在。意义是人的意向性活动,是对事物进行感知和思考来得出的。但同时,意义又为人类建构了一个符号场域,一个生存的环境,并帮助人们在这个环境中确认其自身。人为现象世界规约了意义,并在其中确立了自身的位置。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来自对外界符号的理解,语言是符号最重要的表现方式。“‘语言是存在之家’不是说存在‘在’语言中,而是说世界的意义及其真相是由语言来建构、揭示和看护的。”①这也说明符号的意义建构对世界和自我的重要性。
《坛经》中有一段记载:“(六祖慧能)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磐经》。时有风吹旙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日:‘旙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旙动,仁者心动。’”②意义是由人自己来给予解释的,所以说人心不变,实际上是指对符号意义的解读不变,意义不变自然万物就不变了。人本身即是一个符号,自我亦是符号,人对万物的解释构筑了其自我的意义。阐释的标准相对稳定也就维持了其自我的相对稳定性。结合时间的符号来说,自我存在于时间之中,意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自我作为一个符号是通过意义来进行与外界的交流和对自我意义的建构的。因此,时间改变影响了意义的阐释,同时也不断塑造新的符号自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