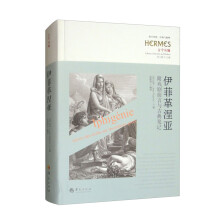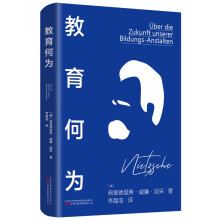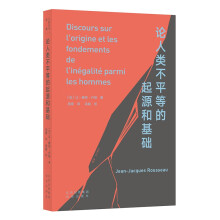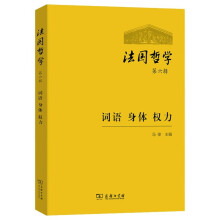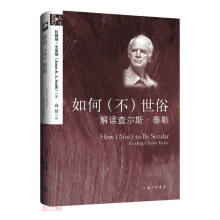斯威夫特的《木桶的故事》显然与智慧息息相关。《木桶的故事》以其精巧的层次首先讽刺了17世纪末英国“才子们”创作的文本。1695年,限制印刷出版的《出版许可法》(Press Licensing Act)失效并且没有再度施行。结果,格拉布街创造出来的作品铺天盖地,斯威夫特的文章直指这里出产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基督教在欧洲发展历史的寓言,由三个儿子(分别代表天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演绎,他们忙于(错误地)阐释亡父留下的遗愿。但是,这个寓言就其本身来说由五个单独的部分(辩词、出版商致读者,两篇献词、一篇序言)引入,因五篇散记而中断。
这五篇散记对格拉布街所产生的文本及其反响进行了深思。此外,我们还得知,文章的标题借用了水手们在遇到鲸鱼时常用的技巧——往水里扔一个木桶来转移鲸鱼的注意力,以免它攻击船身。通过类比的手法,斯威夫特的文章旨在转移“才子们”的注意力,以免他们攻击共同体这个“船体”。因此,《木桶的故事》采取了一种蛊惑人心、声东击西的方式,目的是为了抵消“由于才子们不断提出的新要求而时时增加的威胁”(I,24)。①因而斯威夫特的文章既讥嘲了这一文类,其本身也属乎其中——但鉴于智慧不牢固的地位,他这篇文章必须辨别真假智慧用以保有讽刺的主旋律,因为讽刺在行文过程中可能有逐渐削弱自己的权威的风险。
我们以为斯威夫特必定会维护他自己智慧的权威,但他却欣然接受了讽刺的腐蚀性力量,反复确保文章能损毁掉权威所可能存在的每一个位置。《木桶的故事》充分讨论了妙趣横生的文本的产生及其阐释,而三兄弟的寓言故事本身就是对这一终极阐释过程的讽喻。然而,《木桶的故事》文本的多重层次并非通过区分严肃话语和讽刺话语来互相彰显。例如,作者在辩词里展开的评论,从不可靠的叙述者(批评家称其为汉克[Hack])视角展开,这种视角存在于角色之外,人们可能认为这样会封闭文本——举个例子,这样一篇辩词可能意味着汉克的言谈纯属子虚乌有,而作者的陈述才干真万确。与之相反,辩词却对一切阐释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此外,用汉克口吻写作的几篇散记质疑了写作的本质,三兄弟的寓言也讽喻了阐释的整个过程。每个“部分”——都变成了文本中的一个元话语——看起来似乎都将进一步引导我们阅读文本,并提供解决疑难困惑的关键,但事实上它们反而增添了解释上的困难。从结构上来看,斯威夫特似乎想要告诫读者,阅读本身就是伪命题。
汲汲于建构文本表现了阅读的焦虑,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被迫在洛克的语言王国中进行交易不可避免的后果。或许我们还记得圣狮之梦——斯威夫特幻想出了一种可以证实其本质的语言,然而他并未设想出任何一条可通达此处的路径。因而,按照洛克的说法,斯威夫特尽管痛苦不堪,但他似乎能充分感觉到自己嵌套进了语言之中。因而从文本的第一部分开始,《木桶的故事》就讽喻了误读的各种惨状。这位佚名作者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道歉。他宣称自己对手稿没有最终解释权,因为出版商发行了一部半成本,作者的一位朋友未获作者授意就将其交给了出版商。事实上,文本早已不受控制——可以说,授权文本的签名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此外,误释如同幽灵邪魅不断动摇摧毁文本的意涵。作者告诉我们,木已成舟;对此前版本进行反驳的批评家显然已经将讽刺的要点抛诸脑后:作者不愿费功夫辩护,仅向读者保证,这个满口诽谤的人所言绝大部分完全错误,至于他强加给的那些意义,作者想所未想;作者也不知道,是不是哪位有品位的正直读者想到了。(《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前揭,页79)
因而,作者告知我们,对这一文本的理解将会变成如何对其进行正确阅读的问题;更确切地说,作者告诉我们,他“仅写给那些具有才智和品位的人看”(同上,页85)。
然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一争论中有着弗洛伊德所谓的“破釜逻辑”(kettle logic):这本书写得不清楚是由于出版商没有发行正确的版本,而我们弄不清楚文本是因为没有才智和品位。一方面,我们被要求以一种信任的态度进行阅读:将自己置人作家的精神意图之中就能发掘作品中的思想并以此证明自己同样拥有智慧。另一方面,作者故意站在隐晦的位置,使得这一切将变成无稽之谈——这不仅是因为出版商和将原稿交付给出版商的那位朋友在构建文本时发挥了作用,还能从文本附录里看出来,附录怒斥了作者给文本增补的一系列注释。这些注释以沃顿( Wotton)的笔名发表,加入了一系列之前的文本注释;虽然这些注释与文本拉开了一定的阐释距离,但双组注释正如多重层次所具备的功能一样,进一步让文本意义变得支离破碎。此外,一般的看法是斯威夫特自己写了两组注解并将其纳入了正文之中。因而,从多个方面看,作者的身份于文本各个层次之中避影敛迹了。事实上,似乎没有人能够全权支配文本。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