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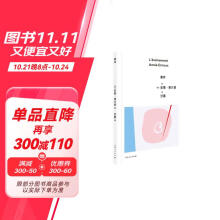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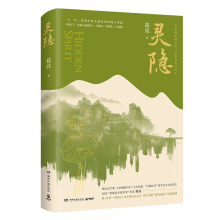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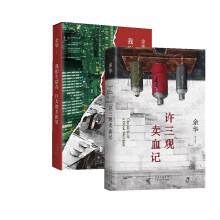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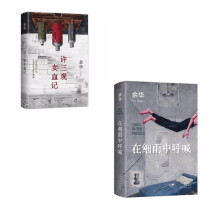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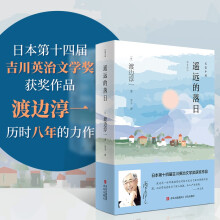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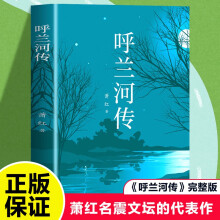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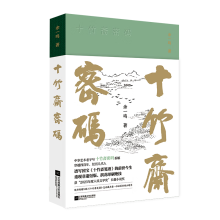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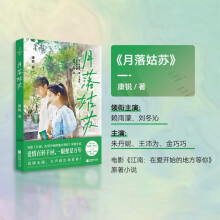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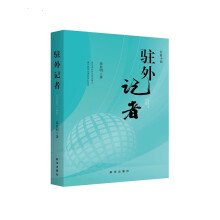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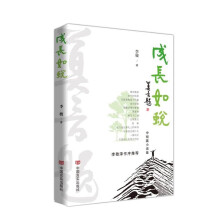
阿拉伯世界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的歌德”纳吉布·马哈福兹代表作
现实主义文学高峰“开罗三部曲”之一
阿拉伯语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作品,200年阿拉伯小说发展漫漫路程中不可逾越的顶点
阿拉伯语文学翻译家陈中耀教授精心打磨的权威译本
以埃及社会为背景,描述了埃及一商人家庭三代人的不同生活和命运,堪称埃及版《家》《春》《秋》。
东方主义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发条橙》作者安东尼·伯吉斯等一致绝赞
完美呈现长篇小说艺术里的复杂叙事、“智慧”和“狡猾”,对政治信仰归属、双重道德等高难度主题的驾驭信手拈来
几个人围着火盆而坐,头凑在一起,伸着手在烤火。艾米娜的双手瘦骨嶙峋、青筋暴突,阿依莎的手干瘪僵硬,乌姆·赫奈斐的手粗糙得像乌龟壳。只有一双手是白嫩漂亮的,那就是纳伊曼的手。一月份寒气逼人,大厅四周似乎都结着冰。不过大厅依然是原先的面貌,地上铺着五颜六色的席子,放着几张沙发,只是原先的煤油吊灯已经无影无踪,现在天花板上悬吊着的是电灯,咖啡聚会的地点也换到了底楼。不仅如此,由于父亲的心脏不好,再也爬不动楼梯,所以楼上所有房间的功能都转移到了楼下。还有这家人能体会得到的变化,就是艾米娜已经老态龙钟,白发皤然。她的年龄虽然不满六十,看起来却好像已过了古稀之年。然而艾米娜的变化与阿依莎的未老先衰相比,那只是小巫见大巫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的头发还是金灿灿的,眼睛还是湛蓝明亮的,但呆滞的目光毫无生气,使人感到造化弄人,感慨万千!这种无神的目光和苍白憔悴的脸色,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她那清癯的脸上颧骨突出、双眼凹陷、两腮干瘪,这怎么会是—位三十四岁妇女的脸呢?至于乌姆·赫奈斐,星移斗转并没有改变她的精神,她依然心宽体胖,只是皮肤松弛了,头颈起了迭皱,嘴角刻下深纹,宛如岁月尘埃的堆积。她那对忧郁的眼睛目睹了这一家人的岁月沧桑,与他们同处于无声的悲痛之中。纳伊曼在她们中间就像一朵开放在墓地里的玫瑰。这位漂亮的姑娘年方十六,披着一头金灿灿的头发,俏丽的脸庞上闪烁着一对湛蓝的眼睛,活像年轻时的阿依莎,甚至比当年的阿依莎更妩媚迷人。她长得苗条柔美,姿色出众,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射出温柔的目光,显示出她的纯洁、天真,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她偎依在母亲肩头,仿佛一刻也不想与她分开。乌姆·赫奈斐在火盆上搓着两只手,说道:
“那幢楼房造了一年半了,这个星期即将竣工……”
“你是说那个卖饮料的比尤米大伯的楼房吧。”纳伊曼的口气里带着嘲讽。
阿依莎的双眼离开火盆看着乌姆·赫奈斐的脸,但对她的话未加评论。往事如烟,玛丽娅嫁给亚辛后不久即被休了,唉,玛丽娅如今在哪儿呢?她的母亲与比尤米结婚后不久去世,现在他半是继承半是购买把原先属于穆罕默德·拉德旺的房产归到了自己的名下,并将它拆除,翻建一幢四层楼房。这些大家都是一清二楚的。当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人人都感到心旷神怡!乌姆·赫奈斐又说:
“太太,这楼房最漂亮的是底层,比尤米大伯新开的店铺,出售饮料、冰激凌和糖果,店堂里都是镜子和电灯,收音机日夜响着。理发师侯斯尼、卖蚕豆的达尔维希、卖牛奶的富里、炒货店老板艾布·赛利阿等人,他们从各自破败不堪的店铺里望着他们旧友的店铺和楼房,真不知有何感想……”
艾米娜把披在肩头上的围巾扎扎紧,说道:
“赞颂好施恩惠的真主!”
纳伊曼搂着母亲的脖子,又说:
“那楼房的墙壁正好堵在我家平台的一侧,那里如果住满了人,我们还怎么能上屋顶平台去玩呢?”
艾米娜无法对漂亮的外孙女提出的问题听而不闻,因为她首先要保护阿依莎。她回答道:
“住多少人都没关系,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她悄悄地瞅了阿依莎一眼,想知道女儿对她这么婉转的回答有何反应。她非常担心阿依莎会受到伤害,所以处处赔着小心。但阿依莎此时正在对着放在父亲卧室和她的房间中间那张桌子上的镜子照看。她依然保持着照镜子的习惯,尽管这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再对自己容貌的改变悲伤。每当她心里有个声音在问她:“过去的阿依莎哪里去了?”她就毫不在意地反问道:“穆罕默德、奥斯曼和赫利勒哪里去了?”艾米娜看着女儿这副模样,心里郁郁寡欢。这种情绪很快传到了早已与这家休戚与共的乌姆·赫奈斐身上,这家人的忧虑也成了她的心病。纳伊曼起身走到放在客厅和餐厅中间的收音机旁,扭动旋钮,说道:
“妈妈,空中歌会的时间到了。”
阿依莎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艾米娜凝视着阿依莎吐出的烟雾像朵薄云在火盆上飘散开去。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声音在唱着:“美好过去的知音,但愿你能够回来!”纳伊曼裹紧身上的长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她像母亲早年那样,酷爱唱歌。她有音乐天才,什么歌曲一听就能记住,并且能用优美的嗓音唱出来。她那压倒一切的宗教情感并没有妨碍这种嗜好。她坚持按时做祷告,从十岁开始就在斋月里把斋,还经常梦见幽冥的世界,外婆让她去拜谒圣裔侯赛因陵墓,她总是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表示欢迎。但与此同时,她却没有放弃唱歌的爱好,每当一个人在卧室或浴室里时,都会哼唱着歌。阿依莎对惟一幸存的女儿百依百顺,她是她黑暗生活中的光明和希望。她既欣赏女儿的虔诚,又赞叹女儿的嗓音,连女儿与她寸步不离——这种依恋显然是太出格了,她也是纵容、鼓励和喜欢,不容别人对它有任何异议。她甚至听不得任何批评,即使是善意的婉转的批评也不行。除了闲坐、喝咖啡和抽烟,她在家里无所事事。如果母亲喊她一起去干活——其实母亲根本不需要她帮忙,而是要为她创造一种从沉闷思绪中解脱出来的氛围——她也会生气,说出她的那句口头禅:“呸,别管我的事!”她不允许女儿动手干活,似乎动一动就让她害怕。倘若祷告也可以代劳的话,她一定会代女儿做祷告。母亲不知多少次跟她谈过这些问题,告诉她纳伊曼已经可以当“新娘”了,应该让她学会“家庭主妇”的分内事情。而她每次都用不耐烦的声音回答说:“你没看到她弱不禁风吗?我的女儿受不了任何累乏,你让她随心所欲吧!除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希望了。”艾米娜以后不再说什么了。她心如刀割般为阿依莎难过。她瞅着她,发现她就是那种万念俱灰的典型,看到她悲伤的脸就知道生活已经对她失去了意义,真是哀莫大于心死啊!因此,她怜悯阿依莎,不忍打扰她,总是习惯以宽大的胸怀、豪爽的同情
心,忍受着她脱口而出的生硬的回答和毫不留情面的话语。
温馨提示:请使用广州市白云区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