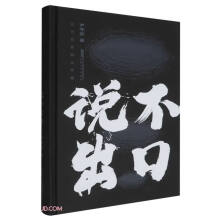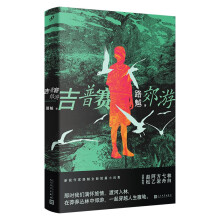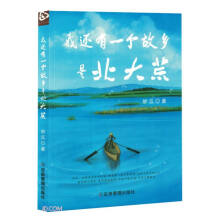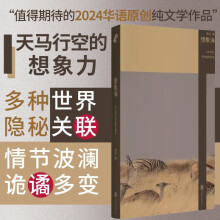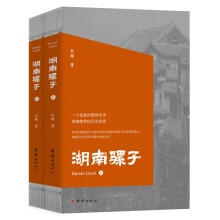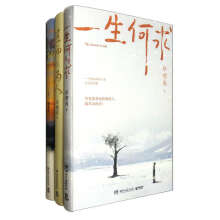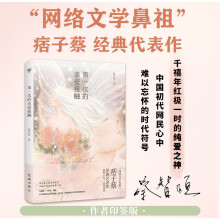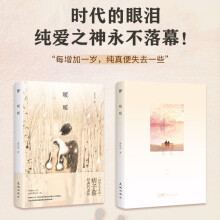一座城的深度
一直以为,以海取地名的地方就在海边,更何况是一个叫观海卫的地方,想象中,站在最高的山巅上,或者爬上城镇的几十层高的楼顶,远眺之下可以观海。来卫城者,不见海涛拍岸,多唏嘘不已,叹道已经看不到大海了,大海与古镇有了距离。
生活在卫城多年,偶然驾车去海边拍拍日出,看渔民扬帆出海捕鱼;或邀上四五个好友,去杭州湾海涂拾小海鲜,晚上烧点海鲜下酒,也算惬意的日子。生活在这个地方,我想搞清楚卫城里的山水历史,真的有点难。于是,摸索了许多年,知道了这个镇的人文历史,这深度远远比大海还深。
一
搬进卫里家园已经有十多年了,算得上一个地道的卫里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总归有自己的思考。我住的小区在波光粼粼的护城河畔,隔河之遥是古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隍庙,楼下的南市路新开张的音像书店、家私广场、家纺服饰、婚纱摄影、发型设计室等琳琅满目,晚上霓虹灯、发光字、灯箱等也光彩夺目,时有新店开张,爆竹声声震天响。站在窗前,往北一公里外有座卫山,山脚下有一个称作卫山风景区的休闲地方,已成了市民晨练的好处所。卫山虽然举目可见,孩提时也常常念叨在口,记忆却未曾光顾,凝望之下,不觉心驰神往。那时,我非常自豪的是,终于成了一个城里人了。
我出生地的老家,是离观海卫五里外的洋浦畔,属于观海卫最西面的一个村落。以前那一条弯弯曲曲流向杭州湾的洋浦,是慈溪、余姚两邑的分界线,这条大浦,害得洋浦对岸上的余秋雨难分是慈溪人还是余姚人。三十年前,我印象里卫里很遥远,向东步行,卫里离村约五里,向西离余秋雨的故里桥头也五里,向南古镇鸣鹤场距离也有五里,又称场里。这卫里、场里两个特殊的地名,加上少年的懵懂,就喊作了“胃里、肠里”了,好像都是一个人的肚里货,身体里离不开的两块肉。
那时,通往观海卫的只有一条铺满沙石的乡村公路,听说是昔日上海滩大亨、乡贤虞洽卿所造,也就是现今观海卫到宁波的国道。公路两旁种满郁郁葱葱的白杨树,耸然挺拔,看起来高入云霄,树杈上常有乌鸦、麻雀筑巢,忽而扑腾飞入天空。沿着公路,我们一步步走到了卫里。早年的观城车站,简陋得仅是三间小屋搭起来的,往胜利桥走,两边还是绿茵茵的稻田,过了架在护城河上的胜利桥,就是进城了。在卫里的食品店里,我们买了些饼干、糖果之类的吃食,这些食品在我们村庄里是看不到的,买了多少,我也记不清楚了。当时,依稀记得卫里的模样:有一幢二楼的饭店,非常气派,还有日杂百货商店……我们是农村里来的孩子,站在饭店门口,只伸了一下头看里面有什么,而不敢跨进门槛。来去一趟卫里,往返要大半天,这毕竟太遥远了,一年也来不了几次。
小学是在村里读的,就在村里的一座破旧陈家祠堂里,还是一、二年级混合的复式班。后来,盖了村校,就像模像样开始读书,同班有四十几个同学,认识了些字,才知道场里、卫里不是人的肚里货,它们的由来,可大书特书了。教语文的翁老师偶尔讲些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故事,场里、卫里的来历,终于略知一二:卫里是明朝信国公汤和建的,场里早在宋朝置盐场起名的,二者相差几百年。
20世纪80年代初,我考入卫前初中。那一年学校里分快慢班,我还算幸运上了快班。卫前的地名寓意就是卫里的前面,那地方本来有座山,筑卫城需要磡石,遗留下来一池七八亩大的石孔潭。大家在同一班级里一起读书,相处融洽,三十年后,我们的同学里出了一个航天英雄杨利伟的战友某空军副团长、一个市文联的主席。三年初中毕业后,我考入了观城高中,村里小学里出来的就剩下我一人。这是观海卫地区唯一的高中,地处东门街,街市热闹。学校里有座古色古香、口字形的明清古建筑,我们课余在卫城的周围逛街,登浪港山,爬烽火台,寻紫霞洞,城里街街弄弄几乎都留下足迹。我感谢出生在城里的几位同学,他们带着我找护城河东北角的城墙遗址,听街上老辈人讲卫城二总兵、三十六街七十二弄、金头十八穴等传说,听听这些名字,就可以嗅到某种幽深的历史气息,卫城的历史值得我长久地阅读。
P2-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