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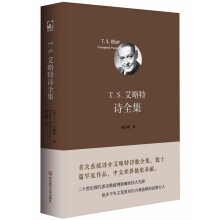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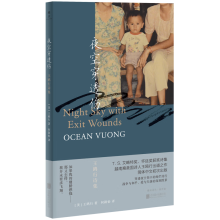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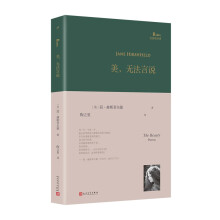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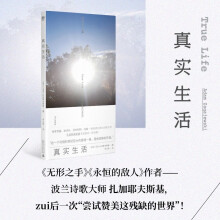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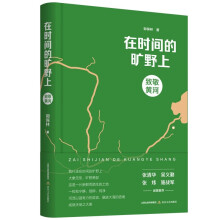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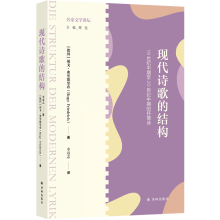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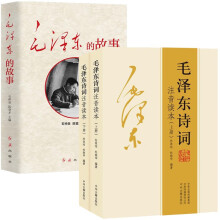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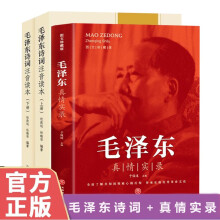
1.词是中国文学的一段精华,王国维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2.二十四位重要词家的生平和作品,串起一部唐宋词的发展简史。
3.既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也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选词独具一格。
4.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畅销台湾四十年,一家人共读的经典。
词是唐、宋时兴起的新诗,它清灵曼妙,注重情韵,能展现中国文化的阴柔美,发挥中国文字的音乐潜能,也展示了抒情传统的魅力。在文学宫殿里,它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形式上的小令、中调与长调,内容上的抒情、叙事与哲理,深深地蕴藉着唐宋词家的生命情调和中华民族一脉而来的情感样态。读唐宋词,感受生命的咏叹。
盛唐的《敦煌曲》
从中国诗史上看,词是很特殊的体裁,它不仅发挥了中国文字的音乐潜能,也展示了抒情传统的魅力。因此,能够跨出唐诗的边疆,在传统文学宫殿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关于词的起源时代与兴起背景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们无意在这上面多所争辩,但希望从一些新的史料加以观察,并略抒一点看法。我们确信,唯有合理地解答上述问题,才能进一步去了解词的发展史与特性。
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1907),甘肃敦煌的秘密正式被揭开,并掀起敦煌学的序幕,这对汉学的贡献毋宁是划时代的。其中有一部分资料曾经使文学史的研究,推向新纪元。特别是《敦煌曲》(约三百阕)对词史久讼不决的问题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新证据,贡献之大,真是难以估计。《敦煌曲》是在敦煌发现的唐人曲子(其实就是词),这些都是从未经著录的作品,由于藏在敦煌石室才得以保存下来。
对《敦煌曲》,尤其是佛曲以外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加以检视,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含有盛唐时代的作品,例如:
绿窗独坐,修得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
想你为君贪苦战,不惮崎岖。
终朝沙碛里,只凭三尺,勇战奸愚。
岂知红脸,泪滴如珠。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
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
待公卿回故里,容颜憔悴,彼此何如?(《凤归云》)
香销罗幌堪魂断,唯闻蟋蟀吟相伴。
每岁送征衣,到头归不归?
千行欹枕泪,恨别添憔悴。
罗带旧同心,不曾看至今。(《菩萨蛮》)
这两阕词的内容都在叙述闺怨,字里行间蕴含着极强烈的念征夫远去的幽怨情绪,与盛唐边塞诗所表现的情调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送征衣”这事件所透露的消息,极为珍贵,从唐代政治史来看的话,将有意外的发现。原来,唐代兵制有三次变革:开始实行府兵制,其次改为彍骑,最后设立方镇之兵。“送征衣”,是府兵制度下的特有现象。唐代府兵制是兵农合一,民无事则耕,有事则战,而当兵所需的衣食完全自备。因为朝廷不 负担士兵的衣食,所以每当秋凉时候,砧杵之声此起彼落地交响着,家家准备送征衣。然而,到了开元六年(718)开始有计划地废除府兵,十一年正式以彍骑取代府兵制。于此可见这两阕曲子是开元天宝时期,也就是盛唐的作品,作者是民间的无名氏。他们以活泼的语言来反映当时征戍的心声,与中国第一部词的总集《云谣集》所展示的情调与社会现实极为吻合,像《凤归云》(征夫数载)与《喜秋天》(芳林玉露摧)等词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说,在盛唐时,词已在民间诞生了。
花间词
至于词的兴起背景,说法也颇为分歧,归纳起来,约有四派:(一)源于《诗经》;(二)源于乐府;(三)源于绝句;(四)源于新声,即胡乐。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必定会牵涉 复杂的问题,包括时代、环境、种族,与文体本身的自然规律等。词,是以本土文化为基础,配合外来文化的刺激,经由孕育而创造出来的新体裁。换句话说,词是中国文化,特别是音乐(自《诗经》、乐府、吴歌、西曲,一脉相承的“里巷之音”)和西域音乐互相融汇整合后的结果。此种文体递变的律则,一如顾炎武所说的:“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日知录·诗体代降》)
的确,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词之所以能跨出唐诗的边疆,不仅是情势使然,更是在上述复杂因素下的必然结果。
词以崭新的形象盛行于民间之后,引起爱好民歌的文人的兴趣,进而模仿填词。在文人的词作里,相传以李白的《菩萨蛮》与《忆秦娥》: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菩萨蛮》)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忆秦娥》)
这两阕词,黄昇称之为“百代词曲之祖”(《花庵词选》)。不过有些词论家却疑为伪作。即便如此,还是不能否定“词起于盛唐的民间,流行于士大夫层面”这一事实。因为,在盛唐或盛唐以后文人填词风气已普遍存在。
至于刘禹锡的《竹枝》,鲜活的语言、乡土的题材,更深具民歌味道。这些例证说明了盛唐以来文人从事填词的事实与兴趣。不过,文人填词所用的语言都具有民间鲜活的气息,词调也都属于简短的小令。
文人层面填词的风气,在晚唐、五代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成果也更为辉煌。当时,中原纷扰,丧乱不已,唯有西蜀、南唐还维持偏安的局面,欧阳炯《花间集·序》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饶之态。”
安定的生活环境与舞榭歌台的情调,助长了词的发展,加上君主(前蜀后主王衍与后蜀后主孟昶)的提倡,使西蜀词风臻于高潮,这可从赵崇祚的《花间集》(共收晚唐、五代词家十八人,作品百阕)得到证明。其中以温庭筠、韦庄两人“薰香掬艳,眩目醉心,尤能运密入疏,寓浓于淡。”(况周颐《蕙风词话》)成就最显著,为花间领袖。他们的作品,像: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
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
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温庭筠《更漏子》)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
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
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韦庄《菩萨蛮》)
圆融巧妙的表现,在词的发展上,象征词体的成熟。尤其是词调与作品数量的增加以及艺术性的讲究,使词成为新兴的独立国度。然而,也因此,文人词逐渐远离民歌的特质,成为他们逃避现实、歌筵舞榭、茶余酒后的消遣工具,难怪《花间集》所透露的大多是绮靡生活中的艳情与闲愁。
南唐的“乐府新词”
与西蜀词坛相比埒,而更具影响的是南唐词坛。由于社会安定,加上君主的爱好与提倡,所以南唐词风炽盛,作家辈出,风格独特。其中二主一冯为核心人物,他们以“乐府新词”“娱宾遣兴”,盛况不亚于西蜀。
王国维曾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又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可见他们在词史上的地位。
后主的词风,由于生活环境的转变而不同,大致上可分为前后两期。开宝八年(975),他三十九岁,是前、后两期词风的分水岭。前期多为欢乐的词篇,以大周后、小周后所交织而成的生 活面,浪漫又旖旎。后期为被俘虏到去世之前的俘虏生活,精神、物质上所遭受到的痛苦是不待言的,这期的词篇,时露家国之痛与人生无常,悲怆凄楚,最为感人。例如: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破阵子》)
至于其他的词篇,像《浪淘沙》《相见欢》等,更是字字带血,句句噙泪。诚然,在政治上,后主是位亡国之君——他没法逃避命运的安排;而文学上,他却是伟大的词家——这可是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大致上说来,后主的词在形式上是真率自然的,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所谓的“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温庭筠)严妆也,端己(韦庄)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即是。内容上,由于诚挚感情的奔迸,不仅是个人一己悲哀的流露,同时也是人类普遍悲情的展示。
“词”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帜
若从地缘来看,西蜀处于边陲偏僻的地方,五代纷扰之际,与外界断了关系,词风也极少与其他各地流通,这种情况与南唐迥然不同。像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人都是来自江西的词家,而江西又是南唐旧有属地,二主一冯的流风余韵对他们多少一定会有影响;就词学的系统而言,北宋初期的词人,完全继承了南唐的遗绪。所以,刘熙载指出:“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
宋朝特殊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使“词”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帜,它的发展不仅反映文体的运作现象,也关系到宋代的生命脉搏。小令的发展,先由冯延巳、李后主的经营,欧阳修(1007 ─ 1072)、晏殊(991 ─ 1055)继承南唐遗绪,到了晏几道而集大成,贺铸是此一脉络的后劲。他们所写的内容大多是悲欢离合与闲愁,以“诗人之句法”(黄庭坚《小山词 · 序》),造成沉着重厚的风格。至于词的创作动机,不仅为了“析酲解愠”,也为了赏玩,所谓授诸贵家歌儿之口,“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小山词 · 自序》)
下面列举几阕词作,借以窥其风貌:
一向年光有限身,
等闲离别易销魂。
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
落花风雨更伤春。
不如怜取眼前人。(晏殊《浣溪沙》)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
草薰风暖摇征辔。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
楼高莫近危阑倚。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莎行》)
曲磴斜阑出翠微,西州回首思依依。风物宛然长在眼,只人非。
绿树隔巢黄鸟并,沧洲带雨白鸥飞。
多谢子规啼劝我,不如归。(贺铸《摊破浣溪沙》)
由于文人学士的参与,使小令的境界为之提高,而逐渐远离闾巷俚歌的风味,当然也渐渐不被普遍群众所接受,于是,教坊乘势竞造新声,里巷歌谣淫冶歌词,也乘时蜂起。《宋史 · 乐志》云:“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
“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一出,使词风为之改变, 他一扫卑视里巷歌谣的心理,不惜士大夫的唾骂,为教坊乐工填 词,因为他善于利用民间俚俗的语言和铺叙的手法,完成声调靡曼的“慢曲”,因此,他的歌词不仅盛行倡馆酒楼,民间也风靡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云:“柳耆卿(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在柳永《乐章集》里,共有二百阕词,用调一百三十左右,小令只有三十余调,全集有十分之八都是长调。这种数量是前所未有,而且他写长调技法高妙,其长篇巨幅,开阖变化,已达运用自如之境。在叙述伤春惜别,室内身边之外,也写出更深曲的情感,更开阔的境界。冯煦云:“耆卿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宋六十一家词选 · 例言》)
柳永的尝试使歌词(口语化)又与民众接近,而“变旧声作新声”,更使词体恢张,有驰骋才情的余地。但他仍然脱不掉绮罗香泽之态、儿女之情,所谓“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艺苑雌黄》)。虽然,他的词都是音律谐婉,却有些“词语尘下”(《苕溪渔隐丛话》引李清照评语),成为《乐章集》的瑕疵。可是瑕不掩瑜,柳永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位写长词既多又好(就数量与品质而言)的人。他的词作,像《雨霖铃》《八声甘州》,写登山临水、望远兴怀,凄清高旷,言近意远;同时音律谐婉,细密妥溜,因此自北宋以来,一直脍炙人口,腾传后世。下面抄录他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
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
方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
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太真外传》云:“上至斜谷口,属霖雨弥旬,于栈道中闻铃声,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可能就慢慢演化成后来的《雨霖铃》曲子,成为一支词牌的名称了。
在现实生活中挫伤累累的柳永,却于词的艺术领域中充分迸放了他过人的才情。在他之前,词的形式仍逗留在简短狭窄的小令里,很难适合委婉的铺叙,缠绵的情致。到他手中,由于精通音韵之美,复擅长抽丝剥茧、细密妥溜、明白家常的表现技巧,使词在长调方面走向成熟的阶段,独到的精神意境更是灿然而生。
这阕《雨霖铃》与《八声甘州》同是他的力作,不论从情景的相生、对比、交融,或结构的严密、造语的寓奇突于平浅来看,都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词作。
要欣赏柳永的作品,不能不了解他那异于常人的毕生漂泊、仕宦不偶、落拓潦倒的生涯,他无论写乡愁或爱情,都梭织着寥落的身世之感,这也就是人们对这位失意的词人倍加怜惜的原因。
《雨霖铃》主要在描写一份爱人间难以割舍而不得不割舍的离情,以萧瑟清冷的秋雨作背景,烘托出人间情爱无比缠绵悱恻的氛围来。通篇字斟句酌,没有一处是掉以轻心的落笔,词人的巧思与功力一至于此,夫复何求?
苏词高处,“出神入天”
北宋前期的词,形式上,不论欧阳修、二晏的小令,或秦观、柳永的慢词;风格上,不论典雅或俚俗,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 的藩篱。内容大都局限于男女的悲欢离合,一己的春愁秋恨与无端闲愁。“靡靡之音”充满词坛,风格更是柔弱无力。他们以游戏态度,在作诗为文之余才去填词,或者由于环境的关系,替乐工官妓而倚新声,往往视为“小道”,不敢自跻“大雅”之林。这种情况到了豪放派领袖苏东坡(1037 ─ 1101)才有突破性的发展。他首先打破传统的狭隘观念,开拓词的领域、提高词的地位、经营词的意境,使词脱离小道末技,达到与诗文同样的庄严地位。胡寅云:“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乎。”(《酒边词 · 序》)
东坡以卓荦不群的自尊、高雅磊落的人格,加上天资学问与豁达胸襟,形诸词篇,造成逸怀浩气的风格。晁补之说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词林纪事》引)刘辰翁也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须溪集 · 辛稼轩词序》)虽然,他的词难免有“不谐音律”(晁补之《词林纪事》引)与“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等攻讦,然而,苏词高处,“出神入天”,足以“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他的词,豪放高旷、清丽韶秀,兼而有之,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例如(《念奴娇 ·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发华。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不仅横放杰出,而且字里行间有自己的人格、学问、情感与思想,这是东坡词的独特之所在。
柳永在形式上使宋词恢张,苏轼在内容上使宋词开拓,在宋词发展上,他们都可说是极为重要的角色。
辉煌的词艺正告示了两宋词的结束
周邦彦的词风工丽,姜夔的词风清空,两人都有相当的成就,而吴文英在两家风格之外,别开奇丽蹊径,他们的词时露“意识流”手法,造成时空错综复杂的效果,将宋词比唐诗,则梦窗似义山。历来词论家对他的表现,毁多于誉,张炎的看法,与沈义父“梦窗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乐府指迷》)一致,直接说出梦窗的晦涩难懂。不过,正如周济所说的“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介存斋论词杂著》),梦窗的晦涩也就是他的特色,那么,对他的代表词作,像《齐天乐》(与冯深居登禹陵)、《高阳台》(丰乐楼)、《八声甘州》(灵严陪庾幕诸公游),恐怕有待仔细去玩味了。
张炎是姜夔、吴文英这一系统的继承者,也是此派词风的后进。他精于词学,强调“词以协律为先”(《词源·音谱》),并认为词要“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他与王沂孙、周密的词,以浑雅、空灵、含蓄见长,笔调委婉曲折,感情低徊掩抑,主题隐晦不明。像张炎的《绮罗香》(红叶)、《西子妆慢》诸阕词就是例证。
就词的音律、形式、风格及表现手法而言,张炎的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辉煌的词艺正也告示了两宋词的结束。
我们不惮其烦地从词的起源时代与兴起背景等问题的探索,到唐宋词风转变的缕析,无非想深刻去了解词的发展史与特性, 从而认知中国文字的音乐潜能与抒情传统的魅力。
【导读】倚声填心曲
上篇 总论
总论
下篇 各家名作赏析
温庭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
韦 庄——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李 璟——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
李 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冯延巳——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晏 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张 先——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
欧阳修——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柳 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苏 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晏几道——今宵胜把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秦 观——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贺 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周邦彦——当时相候赤栏桥,今日独寻黄叶路。
李清照——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朱敦儒——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向侯王?
陆 游——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辛弃疾——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姜 夔——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史达祖——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吴文英——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蒋 捷——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张 炎——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
温馨提示:请使用广州市白云区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我们要走向现代,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寻求一个中国文化的根脉,怎么样重新生根发芽,帮助我们这个社会迈向更好的现代。
——龚鹏程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台湾影响大、水平高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大众学术普及丛书。此后图书一版再版,加印不断,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大陆九州出版社引进后,经一年多时间编辑,今年起陆续推出简体增订新版。
这套书从25万册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整理出60部“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被翻阅的”经典,包括六经及诸子、文艺各领域。当时台湾出版人高信疆、柯元馨夫妇遍邀名家为之疏解,其中有著名学者龚鹏程、傅佩荣、曾永义等,另有知名作家张晓风、传媒界大腕詹宏志参与。60多名专家学者联手,倾力打造,一时风动岛内,家喻户晓。
——《人民日报》2018年04月20日
本次丛书的大陆再版,以2014年的台湾版为底本,每一本都由作者或编者做了修订,质量进一步得到完善,且增加了《易经》与《大学•中庸》两本书。装帧设计上也有创新,开本的设计便于携带,更适合青年读者阅读。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