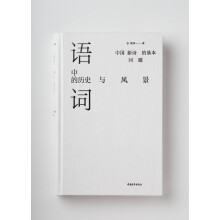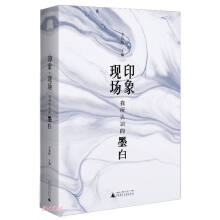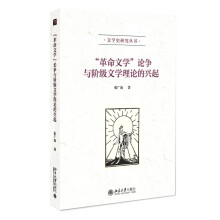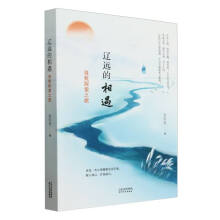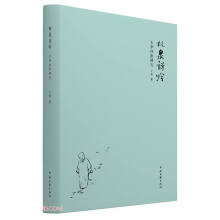《文学与美学的深度与宽度》从两个方向发展:要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有更深入的思考,要将文论和美学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大。
在书中,有一些对古老话题的新的思考。例如“形象思维”问题,考察其讨论的历史,说明这个问题的出现,与对“艺术”与“认识”的关系的理解紧密关联。“艺术”曾经是“认识”.后来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认识”,再到后来“不是认识”。我认为,还有下一个阶段,即“还是认识”。这篇文章还进一步讨论,“形象思维”是如何融化到当代艺术理论的建构之中,分别影响了文艺心理学、古代文论中的“意象”理论,以及人类学关于原始思维的探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符号论思维的建议。还有,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面向当下的争论,需要重新厘清。理论要接地,要联系实际,但理论又要维持自身的理论品格;理论要从实践中生长起来,理论也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历史。这些本来都是常识,但在今天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有必要再次梳理和阐明。
中国文论和美学的建设,都面临着怎样处理“中西”与“古今”的问题。那种认为“中”等于“古”、“西”等于“今”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不能在理论建设中持中西二元对立的立场。要建立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文论和美学,这种努力说说容易,做起来就很难。在学术界常常有各种偏向,而有偏向并不无偏激的理论却常常更具有煽动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