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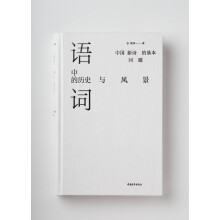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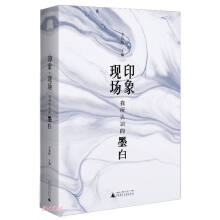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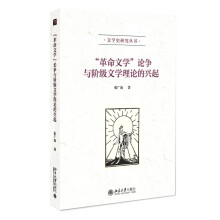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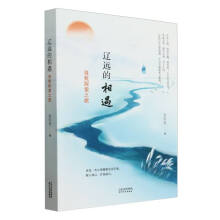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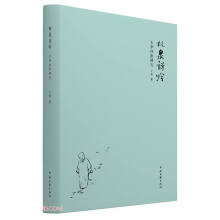
《昭明文选论考》汇集了力之先生的“文选学”研究文章近30篇。全书以“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为研究方法,对《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文选》的成书状况、文选的编者问题、《文选》的成书时间、《文选》的分体等“选学”中的难题做了新的探讨。
近百年前,陈寅恪先生曾有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这两句诗如实刻画了当时中国文史之学的囧境与尴尬。快一百年过去了,一方面我们高兴地看到距离在缩小,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距离之缩小并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么大,某些方面差距甚至在扩大。然而,在这部《昭明文选论考》中,我们愉快地看到刘汉忠教授广泛吸收中、日、韩学者的“文选学”研究成果,并尝试解决《文选》成书问题、《文选》作者问题等国际公认的“文选学”难题。
相信作者在书稿中提出的“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而就原典本身察是非”的研究方法及用此方法得出的诸多结论,对包括《文选》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都会有启发意义。
本书收录作者最近20年间有关“选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别为三编。上编“关于成书及分类研究之方法问题”,主要论《文选》成书研究之方法,如“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中编“编者及编撰的其他相关问题论考”,主要探《文选》的编者及其编撰之相关问题,如《文选》与《文心》工作量之可比性、萧统批评《闲情赋》而《文选》录《神女》诸赋、“五臣注”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之分类;下编“作品诸问题论考及其他”,主要辨析《文选》中之某些作品的若干具体问题,如《赠白马王彪》之题是否编纂《文选》时改、《高唐》《神女》二赋之序的性质。本书着力解决的是“选学”中之难题,而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对相关文献解读之不同,故在一系列问题上,本书的观点与学术界普遍之看法每多殊异。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选)
二、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
古人处理文献的不少做法与今人异,如在古人那里,引书——经传时或不别,如《史记》引《左传》《公羊传》往往以《春秋》称之(《文选》卷46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下,李善注之“《韩诗》曰:‘三月桃花水之时……祓除不祥也’”,亦如是);以一书或一书的某部分的首篇代替该书或该部分,如以《关雎》代替《周南》等;引某一书,如用“《诗》曰”可将“三百篇”的不同诗作之诗句合在一起,如《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之“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按:前者出《鲁颂·閟宫》;中者见《小雅·六月》;后者引《小雅·出车》)[1];引文时有合序文于所序之作品者,如《文选》卷54刘孝标《辩命论》“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下,李善注引“《韩诗》曰”之“《采苡》,伤夫有恶疾也。《诗》曰‘采采芣苡,薄言采之’”[2](此合序文于所序之诗,而两者所出不同。又,“采苡”乃“芣苡”之误,参李注引“薛君曰”);等等。因之,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与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以古还古以究《文选》的成书状况
笔者曾说:认为“《文选》成书仓促”之种种理由,均难以支撑“《文选》成书仓促”说。[3]而辨析这些问题除用跳出《文选》究《文选》与就整体考察部分之法外,用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与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之法,同样能很好地证明这些被认为是“《文选》成书仓促”之理由,多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问题。这里,拟就《文选》“赋”“诗”在设类、分类与作品归属诸方面的问题略作辨析以明之。
在后人的眼里,《文选》“赋”“诗”二体,尤其是后者,其分类标准与作品归属诸方面均存在问题。关于分类标准,站在后人尤其是现当代人的立场上看,作品分类的标准应该是同一的。然其“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24类之分,却并非如此。[4]不过,这与成书是否仓促并无瓜葛。如任昉《文章缘起》序次为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赋、歌、《离骚》、诏、策文、表、让表……《解嘲》、训、辞、旨、劝进……哀策、哀颂、墓志、诔、悲文、祭文、哀词、挽词、《七发》、离合诗、连珠、篇、歌诗、遗令、图、势、约等85类,[5]而这正如游志诚先生所说的“标准不一,有依题材分,依体式分,依作法分,依性质分”[6]。又,本来文体分类越后越分明,而白居易《与元九书》有云:“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谓之‘讽谕诗’。……谓之“闲适诗”。……谓之‘感伤诗’。……谓之‘杂律诗’。”[7]即这前三者以内容为依归,后者则从形式上着眼。又,李善注《文选》卷11孙兴公《游天台山赋》的“朱阙玲珑于林间”与卷30谢玄晖《始出尚书省》的“玲珑结绮钱”,而分别云:“晋灼《汉书注》曰‘玲珑,明见貌’”与“晋灼《甘泉赋注》曰‘玲珑,明见貌也’”。其实,前者为晋灼注《汉书·扬雄传》中的《甘泉赋》语,即“晋灼《汉书注》”与“晋灼《甘泉赋注》”完全是一回事。至于作品归属问题,同为“和”者如卷26“赠答”有颜延年《和谢监灵运》,而谢玄晖《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和徐都曹》《和王主簿怨情》与沈休文《和谢宣城》入卷30“杂诗”;均为跨类的作品,如谢玄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与沈休文《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前者入卷26“赠答”,后者则录于卷27“行旅”,等等。问题是,这些做法即使无所本,亦不出“知山知水”之域。说到底,以《文选》“赋”“诗”二体在分类标准与作品归属诸方面存在所谓问题,而以之归于成书仓促,乃缘忽于以古还古之方法所致。
(二)关于《文选》摘史辞以为所录作品之序的是非问题
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文选》摘史辞以为所录作品之序本不是问题。不过,自两宋间之王观国认为昭明太子这一做法为“误”以还,尤其是现当代学人时或有如是观者。然在笔者看来,这主要的是未能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并把该问题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所致。说到底,这更多的其实是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何以言之,因为摘史辞以为所录作品之序或类此者,在清末以前乃十分普遍的现象。[8]换言之,此与《文选》成书如何无任何瓜葛,以此为《文选》成书仓促之一个理由,乃研究者之疏忽或缘其思之有所未密。另外,学者或因此而说这是昭明太子在《文选》编辑上的“最严重的缺点”[9],则可谓未达一间。即没有注意到在这一点上,古今做法之差异。
(三)关于李善因某题名与“集”异而谓其“误”的问题
李善因“集”与《文选》所录之题目不同而有“误也”“误”等之说,而此中实多为崇贤之失者。学者或以此为仓促成书所致,失之远矣。究其所以然,同样的,乃因未能以古还古而将“异”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我们知道,《文选》所录作品之来源,其与崇贤所见该作者之集的来源时有不同。此其一。其二,这些诗文有的原本无题,有的被其后的收录者作过不同程度之改动。如“杂歌”类录自《汉书·高祖本纪》的汉高祖《歌》,若汉高祖有集,或据《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归,过沛……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而作《歌诗》;或据《汉书·礼乐志第二》“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而作《风起诗》;或据《史记·乐书第二》“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而作《过沛诗》(或《三侯之章诗》);等等。又如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下《班固传》之《东都赋》所附的《白雉诗》云:“《固集》此题篇云:‘《白雉素乌歌》’,故兼言‘效素乌’。”我们能据《班固集》来断《东都赋》此处误吗?况且,就《文选》本身言,其卷38殷仲文《解尚书表》,卷目作《自解表》;卷39司马长卿《上书谏猎》,卷目作《上疏谏猎》;同卷枚叔《上书谏吴王》,卷目作《奏书谏吴王濞》;等等。而今人之未明于此与夫疏忽者,或以此为昭明太子的问题,或以此为《文选》仓促成书之一证,是均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矣。
[1] (汉)司马迁:《史记》卷110,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2页。
[2] (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影印李注胡刻本),第748页。又,后引《文选》而不标明者均此。
[3] 力之:《关于〈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
[4] 参胡大雷(《文选诗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431页)、洪顺隆(《〈文选·咏怀诗〉论:与我的六朝题材诗中的咏怀诗观比较》,载《文选学新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32页)等先生之说。
[5] 今传本《文章缘起》大致保留任昉《文章始》的内容。参吴承学、李晓红《任昉〈文章缘起〉考论》,见《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6] 游志诚:《昭明文选学术论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149页。
[7]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4页。
[8] 力之:《关于〈文选〉“摘史辞以为序”之是非问题》,《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2010〕。又,王观国在《学林》卷七《古赋序》中,一云:“《文选》载扬子云《解嘲》有序、扬子云《甘泉赋》有序、贾谊《鵩鸟赋》有序、祢正平《鹦鹉赋》有序、司马长卿《长门赋》有序、汉武帝《秋风辞》有序、刘子骏《移书责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辞也。昭明摘史辞以为序,误也。”一云:“杨子云《羽猎赋》首有二序……详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赋也。”(田瑞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0—221页)。于此,王氏亦疏矣:“第一序”亦“昭明摘史辞以为”之。
[9] 赵福海等主编:《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又,至于顾炎武、程千帆等氏主要因《长门赋序》提及“孝武陈皇后”而认为《长门赋》非司马相如作,可谓“千虑一失”。参力之《〈文选·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无疑辨》,见作者《〈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
序
上编:关于成书及分类研究之方法问题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3
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 就原典本身察是非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之二 28
关于《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
——兼论《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方法 49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文选〉分体三种说论衡》之三 70
中编:编者及编撰的其他相关问题论考
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 99
关于《古今诗苑英华》的编者问题
——兼说无以动摇《文选》为昭明太子所独撰说 114
《文选》研究四题 124
何思澄任秣陵令及致太子手令于何胤之时间辨
——《文选》编者与编纂时间诸问题杂考之一 138
论《文选》与《文心》工作量之可比性诸问题 154
从对《文选》作品的接受入手难断其编者是谁 173
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
——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 192
萧统责《闲情赋》而《文选》录《神女》诸赋之因探
——兼论两者之异非因各自成于不同的时间 213
关于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选序》“略以时代相次”之“略”
——兼论以此本所出为李善分卷前的三十卷本说难以成立 233
“故意抛出《文选》非昭明所撰之论”说辨证
——读林大志先生《〈文选〉编者问题的重新思考》 246
《文选》所录部分诗文直接来源于史书说 266
关于《文选》篇题和卷目的差异与其文献价值问题 293
关于“五臣注”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之分类问题
——无“符命”“史述赞”与“百一”“游仙”乃后来之失辨 314
下编:作品诸问题论考及其他
《赠白马王彪》之题非萧统编纂《文选》时所改 339
关于曹彪黄初四年是否曾封白马王的问题
——兼论《文选》所录之《赠白马王彪》乃原题 346
论“于圈城作”非诗题而此“集”为再编本
——《文选.赠白马王彪》改自“于圈城作”异议 369
《文选》刘孝标徐悱作品之作时辨
——《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异议及其他 392
宋玉《高唐》《神女》二赋之序为史辞辨 409
关于《文选.高唐赋序》与相关文献之同异问题
——《高唐》《神女》二赋序研究之一 429
《文选.赋》题注与作者注引文辨证四题
——李善注与“五臣注”引文研究之一 448
班固“北地人”辩证
——以《文选》李善注所引范晔《后汉书》为核心 469
附录
《文选文研究》序 489
《汤炳正书信集》序 496
《听罢溪声数落梅》序 503
后记
温馨提示:请使用广州市白云区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刨根问底、严谨细密、新见迭出的学术佳构。它不仅属于现在,而且属于未来。相信热爱学术的人们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在我们的时代有如此优秀的学术著作出现,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拥有力之这样的学者,更是我们时代的奢侈。一切都将成为历史,历史自有定评。
力之先生固非一世之人,而此书亦非一世之书。
——范子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