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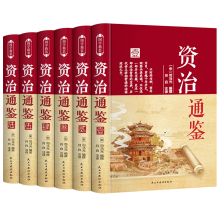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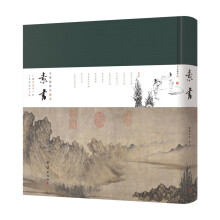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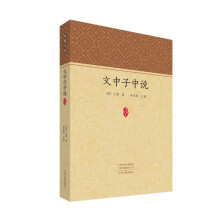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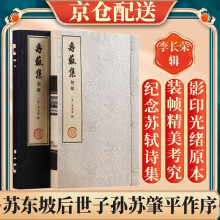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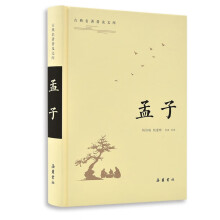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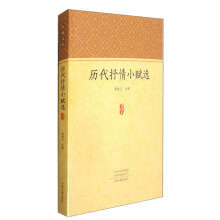

把苏东坡一生宦海沉浮,生活喜乐,娓娓道来,如见其人
凤凰出版社刊行莫砺锋作品
《诗歌与道德名言》
《唐宋诗歌论集》
《漫话东坡》
《莫砺锋说唐诗》
《宁钝斋杂著》
《莫砺锋文集》
《江西诗派研究》(待出)
本书既非随意的“戏说历史”,亦非传统的“学术专著”,而是一位言必有据的学者满怀深情地向读者介绍其心目中真实东坡的通俗读物。虽是以生平事迹为主要内容,却不以岁月为序,在结构上有意用共时性取代了历时性,便于读者从各个不同侧面来观察东坡,从而获得更加全面、鲜活的印象。作者笔下的东坡形象不仅是朝中大臣、地方长官、文人学士,而且是深情绵邈的丈夫、慈祥可亲的父亲、诚恳坦率的朋友、好饮而易醉的酒徒、见到好纸好墨就手痒的书家、戴着斗笠在田间踏歌的逐客、至死不肯皈依西方净土的俗人……
... ...
跋一
我热爱东坡。我爱他的古文、诗词、书法和绘画,我更爱他这个人。可惜予生也晚,没能成为东坡的同时代人,既然“萧条异代不同时”,便只好“怅望千秋一洒泪”了。自从有了东坡,持有这种心理的代不乏人。早在金代,诗人高宪便自称:“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之。”清人尤侗则自许说:“吾不知前生曾登苏门,在四学士之列,与髯公相对几年否?”那么,如果我侥幸与东坡同时,我又将做些什么呢?我当然不敢妄想象尤侗那样置身于四学士之列,但我肯定会像高宪一样不远万里前往拜谒。我情愿长期侍奉东坡,只要能在他身边磨墨铺纸、递茶送水,也是三生有幸。我对东坡身边的人群作过仔细的考察,我有信心到他那里当一个合格的门客或书僮。我早就选准了下面两个“竞争上岗”的对象:一是马正卿,他曾在汴京做过“太学正”的官,学问当然远胜于我。但是马正卿辞官后跟随东坡多年,未见有何功劳可纪,以至于东坡到黄州后才作诗及之:“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我今反累君,借耕辍兹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可见马正卿*重要的贡献就是在黄州帮助东坡开荒种稻,但是收成欠佳。我曾在江南水乡种过七年水稻,插秧、割稻都是一把好手。要是让我到黄州去帮东坡种稻,一定不会输给马正卿!二是刘丑厮,他是东坡在定州时收下的一个书僮,当时是个年方十二岁的穷小子,尚未开始读书。我虽然才疏学浅,但毕竟是个文学博士,要是帮东坡翻检书籍或誊录文稿,总要比刘丑厮强一些吧。可惜这些美好的愿望只是痴想而已,东坡早在九百年前就已“羽化而登仙”了!既然如此,我除了阅读东坡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以钻故纸堆为业的专业工作者的时候,我对东坡与王安石在新、旧党争中的是非恩怨还不甚了了,但在感情上已坚定地站在东坡一边了。1974年初冬,身为插队知青的我偶然路过镇江,初次走进闻名已久的金山寺。没想到刚进寺门,便看到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上面的大字触目惊心:“彻底揭开反革命两面派苏轼的画皮!”寺内还张贴着许多大字报和漫画,揭露东坡的“罪行”。说东坡是“反革命”,我倒能理解,那个年头,只要与儒家沾点边的历史人物,都难逃这个恶谥。但是为什么说东坡是“两面派”呢?我好奇地浏览了几张大字报,才恍然大悟。原来东坡在新党王安石执政时反对新法,后来又在旧党司马光执政时反对全盘废除新法,所以是“两面派”。但是这样的“两面派”不正是大公无私、风节凛然的政治家吗?而且,为什么要在金山寺里批判东坡呢?难道因为东坡曾在这里写过《游金山寺》的著名诗篇,他又是金山寺高僧的座上客,所以要“就地消毒”?我百思不得其解,又不敢向旁人询问,只好把疑惑埋在心底。
天道好还,人们被迫说谎或沉默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我终于可以公开说出对东坡的热爱了。可是我用什么方式来表白呢?跑到大街上去对行人宣讲东坡的事迹?还是到金山寺去张贴赞颂东坡的大字报?好像都不可行。于是写一本书来介绍东坡的念头,便在心头油然而生。杂事猬集,岁月荏苒,这个念头很久都未能付诸实施。1999年,我应春风文艺出版社之约,与弟子童强合作撰写了一本题为《苏轼》的小册子。由于出版社只让写五万字,未能畅所欲言。去年秋天,我应邀到香港浸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每周只要到学校去讲一次课,其余的时间都可待在位于半山腰的穗禾路宿舍里,也没有什么“科研计划”。环境十分幽静,只有小鸟偶然到窗口来窥视,终日无人打扰,连电话都很少。于是我动笔写起这本《漫话东坡》来。我把浸会大学图书馆里有关东坡的图书尽行抱回宿舍,一头扎进东坡的那个世界。以前对东坡的作品通读过好几遍了,材料比较熟悉,窗外的青山绿树和晨曦夕霞也都助我文思,下笔相当顺畅。我从去年十月底开始动笔,等到一月底离港返宁时,电脑里已经积下十万字的文稿了。回到南京大学以后,我不再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写作的速度明显放慢下来。但毕竟全书的框架早已设定,思路也都是现成的,写作的难度并不大。又经过七个月的暝写晨抄,全书终于完稿。我总算实现了多年的宿愿,我要用二十多万字的篇幅来表达心声:我爱东坡!
跋二
书稿写完了,有些情况需要向读者作些交代。
关于东坡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了,而且佳作如林。单说传记类著作,便有好几种是我很爱读的: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东坡传记的开山之作,此书虽然有不少史实错误,但文笔清丽,对东坡性格的刻划也很生动。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出版了两种东坡传记,一是曾枣庄先生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条理清晰、思辨深刻为特点;二是台湾学者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以材料详赡、考订细密为特点。到了本世纪,王水照先生接连推出两种东坡传,*种是与崔铭博士合著的《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二种是与朱刚博士合著的《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前者是面向一般读者的通俗读物,叙事生动,颇似传记小说,但全书内容都有史料依据,并无虚构的成分。后者是南京大学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虽然也具有传记的性质,但全书主要内容是对东坡的思想进行论析,许多章节的写法与学术论文并无二致。在非传记类的著作中,曾枣庄先生的《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对我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以上著作我都曾仔细阅读,且从中获得许多裨益,谨此志谢。然而我受益*多的还不是上述数书,而是孔凡礼先生所著的《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它是一部长达99万字的巨著,取材宏富,考订精密,钩沉索隐,发明甚多。我对东坡生平事迹编年的处理,基本上都是依据此书。我谨向孔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
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关于东坡的著作,我为什么还要撰写本书呢?*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想向东坡献上一瓣心香。一座寺庙可以接纳众多的香客,无论他们是先来还是后到,也无论他们贡献的香火是多是少,都有资格在佛像前顶礼膜拜。同理,无论别人已经写出了多么优秀的东坡研究著作,都不会妨碍我写自己的书,况且这并不是一部必须创立新说的“学术专著”。
其次,我相信我的书自有其独特之处。这本书虽以东坡的生平事迹为主要内容,却不以岁月为序。换句话说,本书在结构上有意用共时性取代了历时性,所以没有取“东坡小传”之类的书名。我觉得这样可以让读者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观察东坡,从而获得更加全面、更加鲜明的印象。此外,本书除了东坡的政治功绩和文学业绩等荦荦大者之外,还广泛地涉及东坡人生中那些琐细的方方面面,有些内容诸如东坡的日常生活、东坡的平民朋友、东坡对文房四宝的爱好、东坡身后受到三教九流的“扯拽”等细节,别的著作中似乎很少涉及。总之,我并不想严格地按照学术研究的准则来评论东坡,我只想向读者介绍我心目中那位活生生的东坡,说说他的生平事迹,也说说他的喜怒哀乐。换句话说,我想描绘的东坡形象不仅是朝中大臣、地方长官、文人学士,而且是深情绵邈的丈夫、慈祥可亲的父亲、诚恳坦率的朋友、好饮而易醉的酒徒、见到好纸好墨就手痒的书家、戴着斗笠在田间踏歌的逐客、至死不肯皈依西方净土的俗人……
本书是一本通俗读物,还是学术著作?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取了一个含意模糊的书名——《漫话东坡》。说它是通俗读物吧,书中却有不少考证性质的内容,还出现了许多注释。有的读者也许要会心而笑:毕竟是写惯了学术论著的大学教授写的通俗读物,写着写着就原形毕露了。说它是学术著作吧,它的主要篇幅是叙述而非论证,书中涉及的许多材料也不注明出处,完全不合时下的“学术规范”。我把本书写成了这种非驴非马的状态,完全是有意为之。我本是写惯了学术论著的人,关于东坡的学术论文也已写过八篇,我在学校里指导研究生时也一再要求他们严格遵照学术规范来写论文。然而我并不想把本书写成学术著作,我甚至有意避免让有些章节显得太像论文,因为我觉得严肃的学术著作无法充分展现东坡的音容笑貌。当然我也不愿意把本书写得太“通俗”,尤其不愿有丝毫“戏说”的倾向,因为我想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真实的东坡,我应该做到言必有据。前面说过,本书中对东坡生平的把握基本上都是依据《苏轼年谱》等书的,但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发现,有些地方甚至与成说南辕北辙。如果我在这些地方不把自己的考证过程写出来,读者肯定要怀疑我是信口开河,从而影响他们对东坡的接受。为了让读者了解新的说法依据何在,我必须把考证的过程做些简单的交代。至于书中的注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自信本书的全部叙述都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的,虽不敢说“无一字无来处”,但基本上能说“无一事无来处”。我当然可能考核欠精或理解有误,但*没有向壁虚构。非学术性质的读物本不能容纳太多的注释,况且太多的材料来源也使我注不胜注,但是有些罕见的材料要是不注出处的话,也会使读者心生疑惑。为了让读者消除疑惑,并免去自行寻找那些冷僻材料的麻烦,我只好加上必要的注释。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情况是,我引述东坡或其他古人所说的话语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于一般的话语就撮其大意迻译成语体文以合全书的行文风格,但对那些特别精警的言语则照录原文以免减损其韵味。这些做法定会产生文风不统一的缺点,我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读者能理解我的苦衷。
写作本书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肯定不能把它当作学术著作去应付学校的工作量考核,尽管我为它付出的劳动并不少于写一本“学术著作”。另一方面,言必有据的写法肯定会减损本书的可读性,那些习惯于“戏说”类轻松读物的读者也许会掉头而去。但是我并不后悔“自讨苦吃”,因为我想做的就是用通俗读物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一位真实的东坡。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能使更多的人走近东坡。
2006年10月31日始稿于香港浸会大学穗禾路宿舍
2007年8月25日完稿于南京大学南秀村寓所
温馨提示:请使用北海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我热爱东坡。我爱他的古文、诗词、书法和绘画,我更爱他这个人。
我只想向读者介绍我心目中那位活生生的东坡,说说他的生平事迹,也说说他的喜怒哀乐。换句话说,我想描绘的东坡形象不仅是朝中大臣、地方长官、文人学士,而且是深情绵邈的丈夫、慈祥可亲的父亲、诚恳坦率的朋友、好饮而易醉的酒徒、见到好纸好墨就手痒的书家、戴着斗笠在田间踏歌的逐客、至死不肯皈依西方净土的俗人……
——莫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