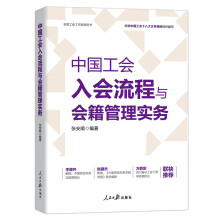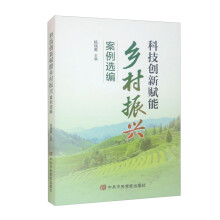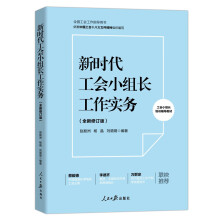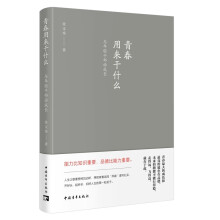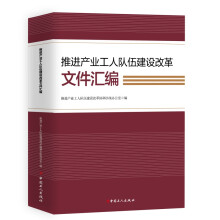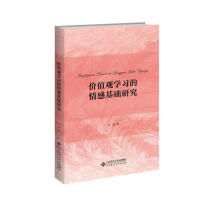技术调整
过去几十年里,关于劳工运动的社科文献研究视角,倾向于单方面强调生产组织及劳动过程的变革对工人力量的削弱作用。然而,正如空间调整一样,技术调整对工人力量也会产生一种相互矛盾的影Ⅱ向。
让我们以20世纪初美国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腾飞时期为例。装配线的引进以及相关技术或组织的变革,让许多工匠的手艺变得过时了,因而明显地削弱了既有工人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能力。此外,资本家突然间也能招募来大量新生的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资本家也能够大幅降低劳动力成本并且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尽管所有工厂都削弱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面对资本时的力量,但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美国规模化生产的工人率先发动了重要的且高度成功的罢工浪潮(首次重要的罢工胜利发生在1936-1937年,也正是大萧条造成大量失业的时期)。
这些罢工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工场层级(workplace)的谈判力量,即工人有能力通过在生产场地的直接行动来造成代价昂贵的生产中断。事实上,20世纪初,这种变革在削弱劳工在市场上的谈判力量的同时,也加强了劳工在工场层级的谈判力量。装配线让相对少数的处在重要位置的工人积极分子,能中断整个工厂的生产。随着一个公司内的各工厂之间生产整合度的日益增加,生产某个关键中间产品的工厂里发生的罢工就能导致所有的下游工厂,甚至整个公司的生产停滞。此外,随着生产越来越聚集和集中,工人停工对资本(有时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经济损失规模也在扩大(Edwards,1979;ArrighiandSilver,1984)。
大部分雪佛兰汽车的引擎都是由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在1936年12月,工人占领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时,展现出了强大的工场谈判力量。通用公司所有装配工厂很快就停产了,公司被迫取消其坚决反对工会的立场,并且与汽车工人联合工会进行协商。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的西欧,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和巴西,以及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的汽车工人罢工浪潮中,同样能见到这种小规模的停工也能对生产造成巨大损失的力量(Silver,2003:第2章)。
工场层级的谈判力量在2010年5月也得到了充分展示,当时,丰田公司四个总装配线中的80%的自动齿轮箱生产是由一个工厂完成,而这个工厂的罢工迅速使丰田的整个生产陷于瘫痪。6月的另一场罢工同样展示了这种力量,一个排气组件供应商再次迫使丰田公司的全部装配业务陷于瘫痪。两次罢工,工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开始于2010年的工人罢工浪潮,不仅提醒人们处于福特主义生产中的工人具有重要的力量,还证明了“全球化”和“后福特主义”的有关变革,并没有像普遍认为的那样直接削弱了工人的谈判力量。绝非巧合的是,上述汽车工人卓有成效的罢工发端于采用“即时性生产”(just-in-time,JIT)方法的零部件(引擎和排气)工厂。即时性生产方法——日本汽车装配工率先采用,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广泛采用——就是装配中只保留少量或零库存零部件,以达到消除冗余、节约资金的目的,而这种冗余正是福特主义的内在构成部分。零部件被“即时”地从供应商传送到装配工厂。然而随着零部件供应缓冲的消除,导致的重要零部件工厂停产的罢工,就能在几天甚至更短时间内使整个公司的装配业务中断。
全球化下的技术或组织变革如何在生产场所强化了工人力量的另一个例子是,随着全球外包生产而出现的紧密整合的供应链变得不堪一击。
资本家为应对劳工强大的工场谈判力量便进一步引进的新技术,旨在促成生产自动化以及减少资本对人类劳动力的依赖,也就是进一步的技术调整。以富士康(鸿海电子)公司为例,它是苹果以及其他大型电子公司的一个主要分包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