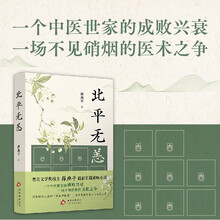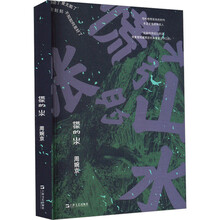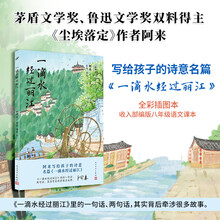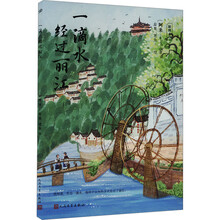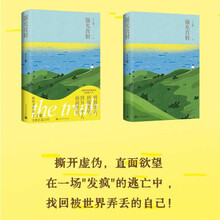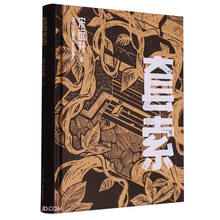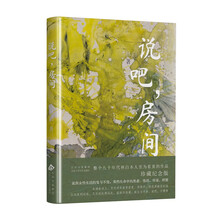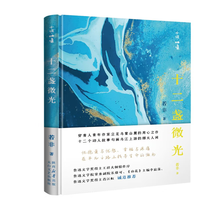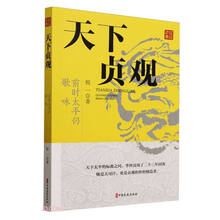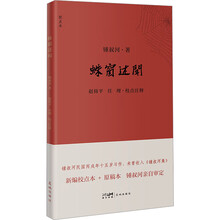黄昏的时候,卫巧蓉走进一片水杉林。通往树林深处的小路逐渐变细,青苔从树下蔓延到路边,她快步走过时,脚步带起了风,缕缕青色的烟从地面上升起,蜿蜒而上,越来越淡,越来越清瘦。她停下来,等烟散尽了才俯低身子凑近看。这些日子阳光好,苔藓干透了,粉末般松散地铺展着,细看起来如一层毛毛碎碎的绿雪,她小心喘着气,担心用力呼出一口气就会把它们吹扬起来。
刚出林子的一刹那,天空似乎亮了一下,像头顶响过一声短促清亮的口哨声。接着,她走上一条布满沙砾的小径,小径尽头就是马路了。街道,楼房,不远处的海岸,浸没在薄暮柔和的光线里,声响也似乎被夜晚悄悄吸附了,四周显得很寂静,是傍晚时分特有的暖金色的寂静。她身后,遥遥的地平线上的山丘只剩下含混的轮廓,挨着山体飘浮的云彩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白,她抬头看时,一朵云正翻过山头,翻到山的另一侧,消失不见了。
剧院伸向天空的几个尖角先露出来。很快,一个透明的多面体完整地出现在视线中。福海剧院到了。跟老家那座蚕茧形的剧院相比,她更喜欢福海剧院的外观,就像不同形状的巨大积木堆聚起来,一道道利落的几何线条,阴天的时候看起来平淡无奇,一有光线就活了,晴朗的天气里阳光穿过大块玻璃拼成的斜坡,透视出一个个宽敞开阔的空间。晚上灯一亮,如海边漂来一块熠熠闪光的宝石,每一个翻光面都粼粼地映着海水的波纹,从远处看过去,宝石像浮在水里,被晃荡着的水波抬起来,又放下去。走到剧院门口时她看看表,离开演还有半个小时,她照例绕到剧院后面,这里有一条木头栈道通往海滩。
海滩的西边是码头。三个月前她在渡口买到船票,上了船,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初春的海风从窗户缝里挤进来,像一蓬细细的针扎向她脸上的皮肤,她从背包里取出围巾,把头和脸裹起来。一直等到渡船靠岸,围巾也没摘下,她蒙着脸,踏上这个初看起来有些荒寂的小岛。那天,海上刮风,天上也在刮风,云彩纷乱,单薄的云身子后面拖曳着一个长尾巴,尾巴的末端已是丝丝缕缕的,像蘸着白颜料的毛笔在蓝天上疾扫而过。
演出快开始了,她推开后门,找到座位坐下,顶上的灯光正好变暗,舞台的帷幕向两侧徐徐拉开。过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了厅里的黑暗,她伸着头四处看,在前几排中央的位置找到了徐季。接着观察徐季身旁的人,左边的男人跟徐季差不多年龄,右边是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他们没有东瞧西望,都专心地看着舞台。有经验的观众已经准备好了,她也把头转回来,望向舞台。
剧院不定期地上演话剧、音乐剧和演奏会。第一次来剧院的时候,她选择的也是最后一排的座位,整场演出她都盯着徐季,徐季也像今天一样脊背挺直,端坐在朱红色的软包座位上,即使只看见他的后背,她也不难想象出他的神情,一种沉入另一个世界的完全的平静。而她不明白台上的人在唱什么,为何流眼泪,怎么又拥抱在一起,从头到尾她的脖子都拧向徐季座位的方向,眼睛在徐季和徐季邻座的人身上转来转去。一直到演员谢幕,徐季也没跟邻座的人有任何交流,他似乎还在静静地回味,演员转身走向后台了他才站起来鼓掌。大多数观众还待在座位附近,她低着头推开后门,顺着螺旋的楼梯往下走。来到门口时她看到柱子上张贴的海报,有出剧的名字叫《吉屋出租》,海报上印着几位异国年轻人,相貌各异,表情都是生动和热烈的,眼睛睁得很大,满怀希望又带点天真地直视着海报外的世界,她站在海报正对面,他们就眼神热切地看着她,好像想对她说点什么。
此刻,她的视线离开徐季,转向正前方。舞台上空无一人,只有幽蓝色的灯光在说话,几秒钟后,乐声响起,泠泠的琴音,悠来荡去,她恍惚看见几杆枝叶稀疏的瘦竹,在空旷的庭院里摇动着,接着琴声变稠,如雨点密密层层地落下来,地上的雨水似越积越多,光一掠而过时照出一汪空明。琴声断绝的地方,更多的乐器走了进来,音量逐渐攀高,水流加快,太阳光轰泄而下,翻折的星空豁然打开,向着无限的虚空延伸,她呼吸急促起来,大水没过头顶,人快要窒息了,乐声终于冲至顶峰,渐次低回,末了只剩下几个零落的音符,像余烬中一闪即灭的火星,最终乐声全部隐去,突然降临的静谧中,一个绿色皮肤的女人出现在光束里。借着乍然一现的亮光,她忍不住把头转向徐季,光线勾画出他清晰的侧脸,脸上的表情跟她之前想象过的差不多。
全部演完总要两个钟头吧,她坐不住也看不进去,一群小猴子在胸口乱蹿,她胳膊交叉在胸前也压不住它们。曾坚信不疑的事实,正变得越来越没有底气,虚弱得站立不稳。头脑中设想过无数遍的画面,即使每个细节都已被磨得发亮,也不会就此变成现实中真切的一幕。
再说,已经这样了,她是对是错又如何,不重要了。
舞台上几个人正围在一起说话,你一言我一语,声调很高,身披大氅的卷发女郎似乎说了一句幽默话,观众席上传来笑声,笑声夹杂着小猴子们奔跑杂沓的脚步声。耳边所有的声响,混合着她脑子里那个似乎永不停歇的声音,让她感觉身体随时会从内部爆开,碎片四处飞溅。她摇摇头,欠身离开座位。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