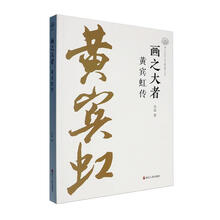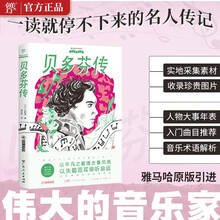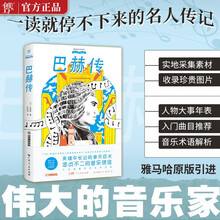《但替山河添色彩:大师吴作人(国际版)/百年巨匠》:
“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
这首由宋代诗人范成大创作的诗歌《横塘》,读上去极具美感,短短几行字,便给我们描绘出了苏州的风景,让我们知晓了苏州的美。
“春天一到,苏州西南的横塘水边绿意盎然,枫桥与寒山寺的塔模样依旧。我不记得多少年了,每年都是在这横塘送客,眼前始终是熟悉的一幕:春雨细如丝,杨柳聚散依依,水边停泊着画船。”
历史上,不少文人墨客都不吝笔墨来描摹、赞美这座城,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里“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白云泉》里“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宋朝诗人范仲淹的《江上渔者》里“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说的都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苏州,小桥流水,精致园林,闻名于世,这不可复制的人文景观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想象,也成就了不少的才子佳人。
1908年11月3日,吴作人出生于此,为苏州添上了一抹新的色彩。
那日恰是农历十月初十,逢慈禧太后生辰,可算得上是良辰吉日,其父吴调元借势讨了这个吉利,给他取名为“之寿”,而“作人”此号,则取自“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一句。所谓“遐不作人”,是说“培养人才谋虑全”,吴调元给自己的儿子取了这么一个号,多多少少是有些望子成龙的意思。而今日看来,这位对中国画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的艺术家,确也不负其名。
仔细说来,吴作人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
祖父吴长吉(1832—1884),号平畴,是名震苏州的职业画师,尤其擅长花卉翎毛;父亲吴调元(1872—1912)先是任职于上海制造局,后又任职苏州县衙司钱粮;祖母杨凤卿(1845—1935)是河北固安人氏,她是原苏州知府杨靖的堂妹,受身边人的熏陶,她本人也渐渐了解知书达理的重要;母亲王宝书(1874—1953)是江苏扬州人氏,虽不是大家闺秀,但也是一位懂得以诗礼传家、以孝悌为本的传统女子。
家中的几位长辈都是读过书且思想开化之人,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吴作人的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然而世事难料,这种思想上的开化,却恰恰成了导致吴家家道中落的罪魁祸首。
吴作人的祖籍本应是安徽泾县,他的祖父吴长吉便出生在安徽泾县的一个小村落——茂林村。许是应了这个村名的景,那里地界虽小,却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多得是学富五车、思想进步的青年,吴长吉便是其中一位。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时,吴长吉十九岁,因其政见开明,倾向维新,便义无反顾地迁居江苏苏州,投奔了当时正在镇守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吴长吉的艺术天赋本就深厚,加之苏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散发着的独特气息,他的艺术造诣越发地高,不久便名声大噪,成为一名著名的职业画师。可惜天妒英才,吴长吉的艺术生涯并未持续太长时间,他便于1884年去世了。
彼时,吴调元只有十二岁,杨凤卿秉承吴长吉的遗愿,含辛茹苦、刚柔并济地抚养、教导他,而吴调元自己也十分勤奋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成年后,他先后在上海制造局和苏州县衙任职,前途大好,只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在新思想与旧思想相互碰撞、新主张与旧制度不断冲突、革新派与守旧派持续斗争的背景下,他成了时代进步下的牺牲者。吴调元与其父吴长吉颇为相像,皆是思想先进之人,因此在革新派主张戊戌变法时,吴调元也牵涉其中,他主张废除女性裹小脚、科举制度等封建制度,极力支持妇女放足、读书,开办新型学校。那些保守派认为吴调元是个不安分的人,将他视为眼中钉,于是密谋在一次宴会中除掉他。1912年,吴调元在宴会中遭到暗算,中毒身亡。
在吴调元被害之前,吴家三代人生活在一起,一家十几口人全都仰仗着吴调元和吴调元的长子吴之屏二人的薪水度日,吴调元为官,而吴之屏亦是收入颇丰的职员,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倒是不错,而这一切,在1912年戛然而止。吴调元去世之后,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便全都压在了吴之屏的身上,每月十八块大洋想要养活一家十几口人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老五吴之翰、老六吴之潘还在上学,而吴作人也即将到了入学的年纪。生活过得捉襟见肘,吴作人的祖母杨凤卿与母亲王宝书不得不开始糊火柴盒以贴补家用。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吴作人的大姐吴之琪远嫁到北方,一年到头见不上一次;三姐吴之琦也成了上海的一户人家的童养媳,离开了吴家。
即便这样,吴家的日子仍然过得十分艰难。但是吴作人的祖母与母亲都深知学习知识的重要,因此哪怕家中入不敷出,还是在吴作人七岁时将他送进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附小读书。吴作人读到三年级时,家中实在是负担不起三个孩子的学费。当时,吴之翰、吴之潘都在上中学,再有两三年就能完成学业,若是此时辍学,便前功尽弃了,两相权衡之下,母亲王宝书只得选择让吴作人辍学待在家中,想着什么时候家中宽裕了,再将他送回学校。
至此,吴作人开始了休学在家的日子,这一休,就休了三年。三年后,吴家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吴作人才得以进入江苏工业专门学校附中继续学习。 “那是一段十分灰暗的时光。”多年后吴作人再回忆起来仍然这样形容。 古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有它的道理的。若是没有那段时光,后来的吴作人或许没有那么大的韧劲儿去面对人生的诸多风云变幻,甚至无法成为几乎贯穿中国画坛整个20世纪的巨匠。 任是吴作人自己,怕是都没有想到,正是在家休学那三年,彻底颠覆了他的人生轨迹。
母亲王宝书迫于家庭困境不得不让吴作人辍学,却并未打算让他停止学习,所以即使休学在家,她和吴作人的祖母仍然会在闲暇时间教授他学习古文,若是赶上她们忙着糊火柴盒,就把吴作人关在阁楼上,让他自己学习背诵《论语》《孟子》《诗经》《离骚》等古文,有时候一关就是一天。
背诵古文本就是一件令人烦躁的事情,更不用说要背上一天,因此刚刚休学在家的那段日子,对吴作人来说,只能用“枯燥”二字来形容。这种枯燥,在他发现了阁楼中那些新奇玩意儿后,不复存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