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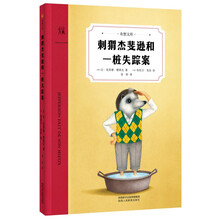
小瓦房建在一个高坎上,高坎用薄如纸片的铜板石一张张精心铺砌,足足垒到十米多高时,才与后面的坡度形成平地,算是打好了地基。从正面看去,房子底下就像压着一个巨大的“千层酥”,煞是好看。墙体所用的砖瓦,是用镇上最好的红土烧成;房梁是自家林子里的老柏树;刷墙所用的石灰也是父亲带人亲自烧制的。小瓦房四四方方,就像切蛋糕似的,被平均分成了四间屋子,每间屋子都有明亮的玻璃窗子,除了底层的四间屋子,还额外建有一层阁楼。我的父母以前是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就在我出生的第三天,一个秋日的黄昏,我们一家三口迁进了这座崭新的小瓦房。
我家门口有一条供两人并排行走的土路,是赶集的必经之路,被称为“大路”。从我记事起,不管谁去赶集,走大路经过我家的时候,都会仰起头来,双颊满是汗水,眼里满是羡慕,他们必定先夸赞一番这房子修得好,再夸赞一番父亲有本事,最后要夸赞的,就是我的命好!
很多人干脆立稳了小背篼,跑到高坎上,借着找水喝的由头,钻进小瓦房里一探究竟,他们眼睛看个不停,嘴里问这问那,争执最多,也是最令他们激动的问题非常统一,那就是:为什么父亲放着那么多平坝子、宽坝子不要,偏偏要费时费力,在这个鸟不生蛋的斜坡上垒出一个高坎来修房子?
父亲微笑着看了看母亲。我母亲心灵手巧,很能吃苦耐劳,可在农村小媳妇中是比较挑剔讲究的。她看中了小瓦房右边这片翠绿茂密的大竹林,更喜欢门口那棵百年老核桃树;我家屋后还有一片可爱的柏树林。把房子修在这里,真算得上是风景如画。
以前这里是斜坡、是荒地,什么也没有,可自从父亲有了这个念头,有了这个承诺,就有了房子,有了家、有了门庭若市。
从无到有,真是一个神奇的过程。
后来,我有了一个妹妹。她胖乎乎的,大眼睛,有点傻,喜欢皱眉。
我喜欢她,她让我感觉自己很大,也很得意——竟然还有一个人比我胆小、比我愚蠢,比我更不懂事。
我们玩得无拘无束:我喜欢在田野的青草里赤脚跳跃,妹妹也跟着我跳;我喜欢在一行翠绿的杜仲树下弹杏核,妹妹也跟着我弹;我喜欢在香气弥漫的雏菊花丛中编花环,妹妹也跟着我编。我还喜欢跑去森林里玩,妹妹也跟着我跑。我的家就在镇上一片最可爱的森林边,只要我想,随时可以一口气翻过山坡,钻进森林。父亲和母亲都不跟我们玩,他们只负责每天站在芭蕉树下,一遍又一遍喊:“姗丫头,婷丫头,回来吃饭了!”
当我们故意躲起来的时候,喊声会一遍比一遍大。
楼房村九组,这个最幸福的家庭,只维持了不到六年。大概老天爷也嫉妒我们了,又一个秋日的黄昏,一声惊雷卷走了我最爱的那个人。
我六岁时,母亲去世了。
从小瓦房右侧的竹林穿过去,有一个小山谷,它是刘家山的一个“褶皱”,由于平地很少,只住着一户人家。父亲大概认为,母亲会喜欢那里,于是将她埋在了小山谷里。
我的永无岛,没有了母亲。
山谷里有一道小溪,旁边是奶奶家的菜地,我常常故意去那儿打泉水、摘豆角、剥青菜。因为母亲的离去,也因为母亲的存在,那个山谷让我觉得无比亲切,就如同母亲一般。
永无岛上,没有了母亲,也就没有了快乐。
我不再爱跑,也不再爱跳,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找谁,只是呆坐在小溪边,盯着溪水和水里的小鱼。鱼的速度时快时慢,有时还静止不动,就像在学我;螃蟹虽然穿着厚厚的盔甲,却常常躲在石头底下,它一般不伤害人,可它如果被逮住了,就会生气地挥舞着大夹子;如果想引诱一只灰蝶,我的方法是捧着一把野花不要动,它吃花蜜的模样就像我在舔白糖;麻雀的巢不止一次被我猜中,但我从不靠近,而是静静等待,它来沟里饮水时会经过我,有时候还会短暂停留;蛐蛐儿向来喜欢首先亮一亮它的歌喉,等你听腻了,才嗖的一下跳出草丛,亮一亮它精致的体格;偶尔还会有蛇,那是我最怕的,一想到它,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一见它,我就会没命地跑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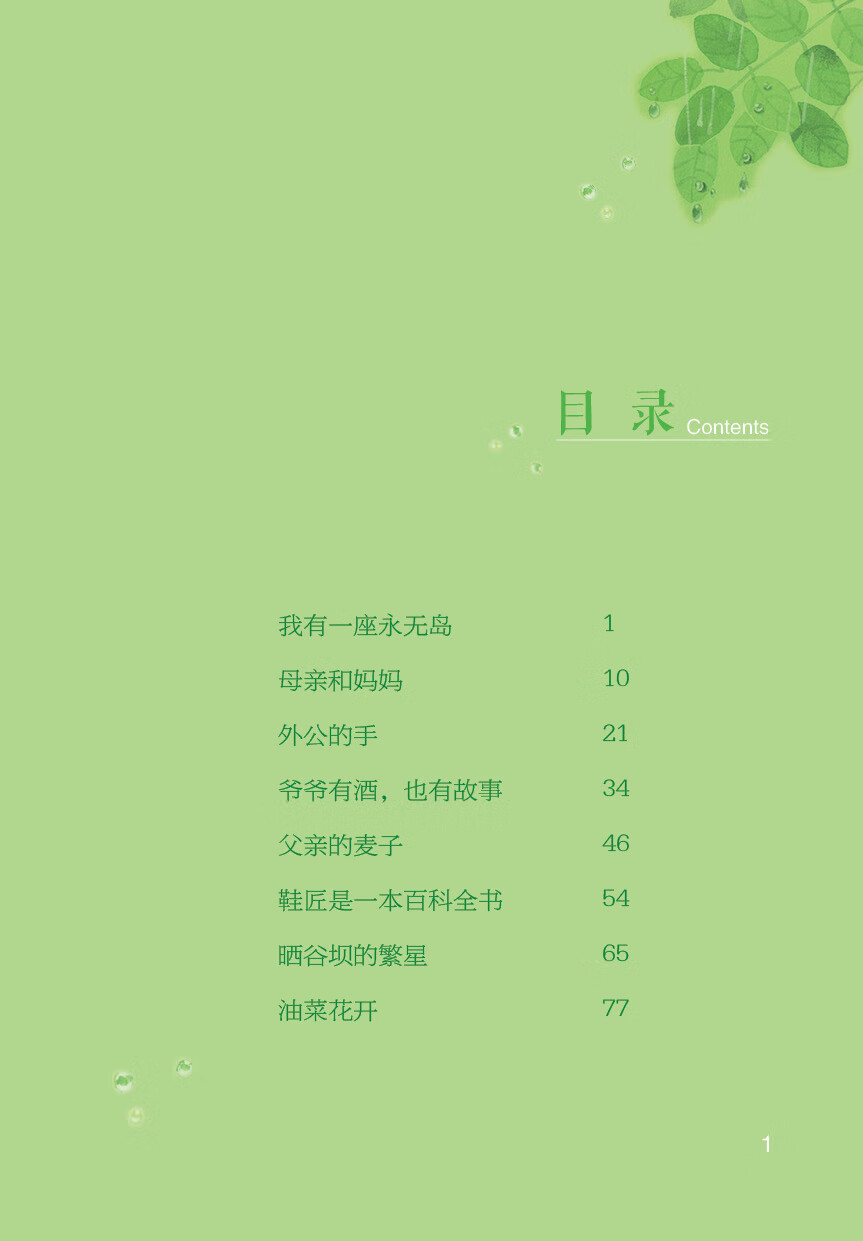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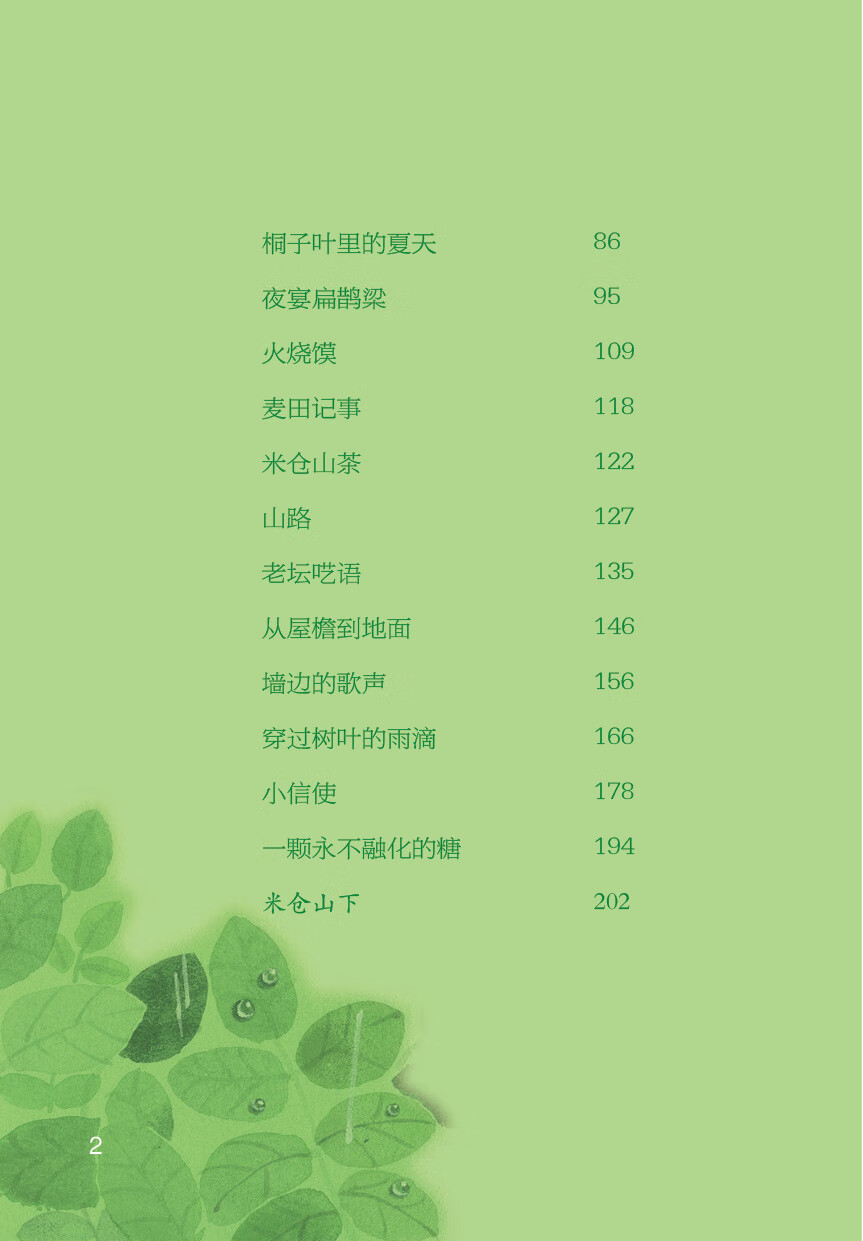
温馨提示:请使用员工书屋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