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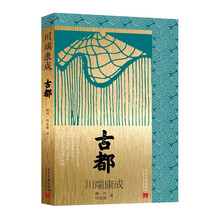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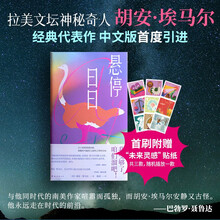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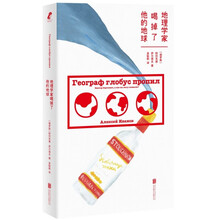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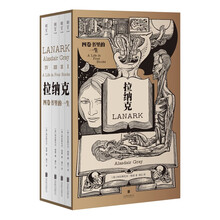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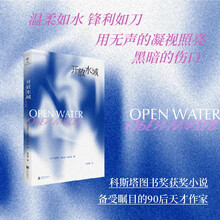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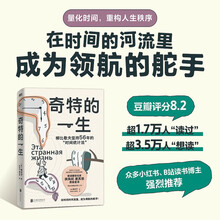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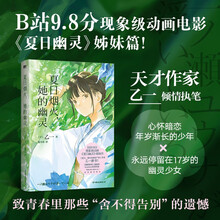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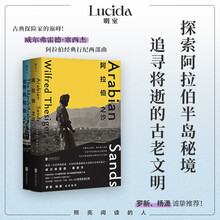
◎ 拉美当代文学大师里卡多·皮格利亚代表作中文版初面世。
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是“拉丁美洲最独特的文学声音之一”,曾获多项西班牙语文学重要奖项。《缺席的城市》是其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已被译为多国语言,曾被阿根廷20世纪重要音乐家赫拉尔多·甘迪尼(Gerardo Gandini)改编为同名歌剧。
◎ 军事独裁政治中的文学抵抗,在一个历史被缺席的国度,有人正力图守护和抢救记忆。
拉美的极权主义的历史由来以久,尤以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最为严酷。本书的故事背景设置在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统治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时期,其间,反对独裁政权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常常莫名失踪。
在书中,当“女身机器”输出的故事传播真相时,警察便试图介入以将之捣毁,从而确保社会话语的稳定和对记忆的抹除。拯救这台机器,就是守护和抢救我们记忆的权利:她是永恒,是流淌着故事的河流,是让记忆保持鲜活的永不休止的声音。
◎ 一段跨越体裁边界的先锋叙事,这是皮格利亚抛出的具无尽魅力的故事之引诱。
在迷人的侦探故事的外衣下,本书也是一个关于爱与失去的爱情故事,一则隐喻被严密监视的压抑现实的政治寓言,一部令人想起威廉·巴勒斯作品的赛博朋克科幻小说。在这里,如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大街小巷,多重的线索相互交叠,消弥着叙事的边界,令故事的魅力无穷放大。
皮格利亚主张“所有的故事都是侦探小说”,他以天马行空的创意对文本进行加密,而读者则化身为侦探去解码。我们阅读这部小说,仿佛可以花上一辈子去解其中的谜。
◎ 一篇伟大作家间的文本对话,这是皮格利亚诗学宇宙的一次丰盈呈现。
除了小说家的身份,皮格利亚亦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在其小说写作中,他常常通过融入互文、戏仿等后现代结构手法与叙事技巧,在与经典作家的对话中,呈现其在真实与虚构、政治与文学、历史与现状等方面的深刻洞见。
在《缺席的城市》中,皮格利亚频繁出入于博尔赫斯、乔伊斯、福克纳、爱伦·坡、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文本,更是对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罗伯特·阿尔特、《神曲》《一千零一夜》等多有指涉。他以精妙绝伦的叙事技巧,让我们一窥其丰盈的诗学宇宙。
后记
我一直喜欢那种有数条并列故事线索的小说。这种情节的交错与我对现实的强烈印象紧密相联。在这个意义上,《缺席的城市》与生活极为相似。有时我会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人在不同的情节之间游走,感受到一天之中,当一个人和朋友、爱人,甚至是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便触发了一种故事的交换,一个多重门一般的系统,打开它便可进入新的情节 —这就像一个我们居于其中的语言网络 —而叙事的核心品质便是这种流动,一种明显的向另外一条故事线索逃逸的运动。我一直试着描述这种感觉,我相信这就是《缺席的城市》的起源。
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机器的故事融入其中。这涉及一个我一直以来感兴趣的关于小说组织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叙事艺术核心要素的中断概念。当我思考“中断”的时候,脑海里会浮现出某些参照,比如山鲁佐德,以及一系列延续此传统的文本,我们可以一直列数到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我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种传统,它将小说视为一种建立在中断的基础上的文学类 型,小说以此为出发点,与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活的经验建立联系 —而生活本质上就是由中断与暂停组成的。
在这方面,另一个我非常欣赏的文本是博尔赫斯的《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这个故事以一种高度浓缩的方式写成,在一个迷宫般的系统中, 总有某个转角将你引向另外一条故事线索。我喜欢将情节比作街道这个想法,你打开一扇门,生活突然就
完全不同了。或许就是受此启发,我决定用城市来比喻小说的空间。
我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某种速度印刻进叙述之中,这一问题无疑与不同故事之间的衔接方式,以及中断、碎片化和暂停等问题有关。相较于我之前的作品,这种关于速度的观念是某种新东西。我试图在《缺席的城市》中实现的是一种极端的凝缩与速度,同时
尽可能地摒弃对反讽的依赖,而后者是我写作中一个自 然而然的特点(譬如,反讽是《人工呼吸》写作中的决 定性标记)。
现在我想再来谈谈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以及他与乔伊斯的相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缺席的城市”这种标题的组合,是这部小说中最具马塞多尼奥风格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它影射了马塞多尼奥的一个基本观点,虽然并非那么显而易见:在现实中缺席的
事物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个观点表达了马塞多尼奥的非实用主义伦理,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一个坠入爱河的男人走过一个属于他的城市,但这个他与他所爱的女人走过的城市却遗失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市是一台记忆机器。当然,那个遗失或者缺席的城市也包含生命中的其他时刻,并不仅限于那些与女人有关的时间。举例来说,这就是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运作的方式。
都柏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类似,它们都是文学之都,两座城市都生活着许多作家(20世纪30和40 年代,马塞多尼奥、博尔赫斯、阿尔特、科塔萨尔等都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作家与都市之间都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譬如,斯蒂芬·迪达勒斯就感受到自身与英语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他认为英语是一种帝国的语言。 类似的,在阿根廷,对西班牙语的承继及试图独立于西班牙的努力,是经常被拿来讨论的。乔伊斯之于莎士比
亚,马塞多尼奥之于塞万提斯,我们可以在这两对关系 中看到很多相似之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语言是谁的语言?以及,我们该如何通过克服与这种语言相关的政治控制以理解,比如说,莎士比亚——考虑到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戏仿——以及马塞多尼奥对西班牙黄金世纪所采取的立场?
乔伊斯和马塞多尼奥之间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某种诗学上的神秘主义。乔伊斯如此写作是为了不被他的同代人所理解,他所设定的叙事方式和语言的使用方式,使其同代人都不可能完全透明地理解他。这种距离本身成为其诗学的一个要素。作为艺术家,乔伊斯不追求同代
人的理解,相反,他为他们呈现了一个谜团。正如乔伊斯本人所说:“我设置了如此多的谜团与疑问,足够教授们针对我要表达的意思争论上几个世纪了,而这是令一个人保持不朽的唯一方法。”
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在马塞多尼奥身上看到。但马塞多尼奥所持的立场,在我看来,比乔伊斯的更为激进。因为尽管乔伊斯花了十七年的时间写《芬尼根守灵夜》,但他最终还是将它出版了。而马塞多尼奥花了近四十五年的时间写《永恒之人的小说博物馆》,生前却并未将它出版。
两位作家都拒绝向社会妥协。我们可以想到一些与社会周旋、建立多重关系的作者,当然也有一些伟大的作家可被归入其列。但也有作家彻底切断了这些关系。乔伊斯和马塞多尼奥身上就带着这些人的影子。他们试图制造断裂,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十分陌生的关系:比如
乔伊斯与供养他的女人,或者马塞多尼奥被朋友所环绕。 谈到文学材料的生产与流通的区别,马塞多尼奥也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十分了解这两个领域的情况,优雅地谈论其区别,并就两者之间的通路建立了一套理论(事实上,这是一种小说理论)。他终生写作,书里充满 写给读者的前言和提醒,以及关于他的书的启事与观点;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看到他拒绝出版。我喜欢这个 例子,马塞多尼奥将自己置于流通之外,不受外界打扰, 遵循自己的节奏。他写作时并不以满足消费者的订单为 标准,他考虑的是那类总是在旧书店拥挤的书架上寻觅 失落文本的读者。
通常来说,我们倾向于从一个文本中推断出某种隐藏的社会样貌,想象文本写作的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与此相反,我在“岛”这一小节中试图做的,是创造一个可能构成《芬尼根守灵夜》的背景的社会。这个社会不是乔伊斯写《守灵夜》时所身处的那个社会,它不指向爱尔兰与英格兰的紧张关系,也不涉及其他一切构成真实文本背景的要素。我想探寻的是:在什么样的想象性背景中,《守灵夜》作为一个文本是有效的?换句话说:在什么样的社会中,《芬尼根的守灵夜》可以被当成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来阅读?答案是:一个语言不断在变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作为一种可能的文学批评的模式一直吸引着我。我认为文学批评应该试图想象文学作品中隐含的、虚构的背景。在这种情况
下,问题就变成了:《芬尼根守灵夜》中隐藏的现实是什么?答案是:一个人们认为语言就是写在文本中的东西的现实。
《缺席的城市》同样如此。你可以说在《缺席的城市》中,我想象了一个被故事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真正存在的是被讲述出来的故事,是讲述破碎的阿根廷故事的机器,我要写的就是一部关于这个社会的现实主义小说。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我在“岛”中对《芬尼
根守灵夜》的化用与整部《缺席的城市》中应该发生的故事之间的联系。
我感受到自己与某些当代作家,比如托马斯·品钦和唐·德里罗,有一些共通之处,说句玩笑话,我将之称为一种关于妄想症的虚构。在某种程度上,它来源于对其他文本的阅读,比如威廉·巴勒斯、菲利普·迪克, 又或者罗伯特·阿尔特。一种关于阴谋的观念普遍见于这些作家的作品,在《缺席的城市》中同样如此。这种观念认为社会是由阴谋所构建的,相应的,也存在反阴谋。这就将问题拉向了与文类的某种关系,拉向了对政治作为阴谋的一种反映。我指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文学;传统政治文学里有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之分,
而政治小说与公共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我指的是,政治与文学这两个类别之间的边界消弭后(也许这就是后现代的定义,公共与私有之间对立的消解,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对立的消解),政治在文学中呈现的方式。当所有这些二元对立都消失的时候,阴谋、 诡计,就会作为主体把握政治在社会中意味着什么的 模式而出现。
……
……
最后,我相信一本书的译者总是经历着一种与其作者的奇特关系。这不仅涉及风格、参考、可能的错误,或者翻译可以对文本进行哪些改动。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翻译所涉及的工作,一方面,翻译是一种不寻常的阅读活动,另一方面,它还涉及一种所有权。我一直对翻译与所有权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因为译者事实上改写了整个文本,这个文本既属于又不属于他 / 她。译者总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奇特的境地,因为他 / 她的工作是将一种既属于他 / 她又不属于他 / 她的经验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作家会引用或者直接复制别人的文本,我们所有人都偶尔这样做过 —因为一个人会遗忘,或者太喜欢那个文本而不得不这样做 —但译者进行的是一项在这两个地方之间画出一条小径的工作。可以说,翻译是一项奇特的挪用活动。
我对文学中的所有权的态度类似于我对社会中的所有权的态度:我反对所有权。我认为翻译中存在一个所有权的游戏。也就是说,翻译对文学常识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提出了质疑,文学中的所有权问题就像社会中的所有权问题一样,事实上极端复杂。语言是一种共同财
产;在语言中,没有所谓的私有财产。我们作家总是尝试在语言中放置标记,看看我们是否能阻止其流动。语言中不存在私有财产,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普遍流动的循环。文学中断了那种流动,而这也或许就是文学的本质。
Ⅰ 遇 见 / 1
Ⅱ 博物馆 / 41
Ⅲ 机械鸟 / 91
Ⅳ 在岸边 / 153
后 记 / 195
温馨提示:请使用员工书屋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