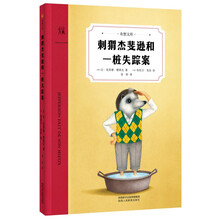解放前,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政局动荡,经济萧条,贪污腐败,欺压良善的现象层出不穷,物价飞涨,搞得民不聊生,最受苦的便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他们不仅受到剥削,还常常受到压迫,别说是民主,就是最基本的民生都难以得到保障,每天都徘徊在生死的边缘。上海这个不眠不休的大都市,鱼龙混杂,到处充斥着物欲和流浪者,就是在这表面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充满了资源分配不均匀、贫富差距极度明显的矛盾。上流社会不仅大肆铺张浪费,还利用职权或者收买官员欺压百姓,盘剥他们的劳动成果;而底层人民却是敢怒不敢言,每天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社会治安大乱,盗窃、绑架、抢劫等事件屡屡发生。这天天还没有破晓,穷苦的人们已经挑上扁担,匆匆走过街头,为一天的生计而奔波忙碌起来。在一个既肮脏又阴湿的弄堂里,一个清洁夫拉着一个木制清洁车缓缓行走在石板路上。
石板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行走起来很是不便。但是一个浑身脏乱,头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黑色帽子,满身补丁的清洁工轻车熟路地避开了地上的沟壑,埋头拉着垃圾车。车子停靠在一堆垃圾旁,清洁工直起腰,揉了揉因为仍有睡意而迷迷瞪瞪的眼睛,深深地打了个哈欠,使劲舒展了下还未从睡梦中醒来的筋骨。感觉身上有了力气,这才拿起靠在一旁的大铁锨,来到已经多得溢出来的垃圾堆旁,将地上的垃圾收拾了一下,便用大铁锨往车里装垃圾。清洁工刚将一铁锨垃圾扔进车里,就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叫声。这里是后街,人们扔垃圾的地方,地方狭小、肮脏又僻静。这声突如其来的孩子的哭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清洁工四处张望,想是自己听错了,也不理会,弯下腰继续往车上装垃圾。
突然,又是一声更大的哭喊声,这声音听上去很不耐烦,显然是不满意被这从天而降的垃圾打扰了。清洁工这次确定没有听错,而且声音是从垃圾车里传出来的,他望着垃圾车,看到刚刚倒进去的垃圾在翻动,从里面居然拱出一个小孩儿。他——大脑袋、细脖子、大鼻子、细胳膊,头顶上长着三撮头发。这就是流浪儿三毛,他在垃圾车里睡了一夜。凌晨的这个时候,正是人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却被人莫名其妙地从美梦中吵醒,还被泼得全身上下都是垃圾,任谁都不会高兴的,三毛从垃圾中挣脱出来,坐在垃圾车上,皱着眉头,噘着小嘴巴,哼哼唧唧地埋怨着别人打扰了他的美梦。三毛扒开身边的垃圾,使劲抖了抖身上的衣服,眯着眼睛找着那个罪魁祸首。
清洁工看到是个孩子,害得自己虚惊一场,看着三毛的样子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惊讶地笑着骂了句:“他妈的!”三毛哪里肯浇,本来被人吵醒已经是很不爽的一件事情,现在还莫名被人骂,一团小火苗蹿了上来,老大不乐意地瞥了一眼拄着铁锨、站在一旁的清洁工。清楚了始作俑者是谁,三毛顿时睡意全消,他瞪大眼睛,毫不示弱地用小手狠抓起一把垃圾,向清洁工扔去:“哦,是你啊!居然还骂人!”清洁工觉得三毛有趣,又小得很,不可能对自己造成任何威胁,故意调侃道:“干什么呀你?”三毛恶狠狠地回了句:“睡觉!”随后就跳下车,回头斜了一眼还在嘲笑他的清洁工,裹了裹身上破旧单薄的衣服,看了眼露出来的腿和光着的脚,在清洁工的骂声中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街口。
天亮了,整个上海又像活过来了一样,大街上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到处都是拉人的黄包车,拥挤在街道上,像一条川流不息的“黄包车河”,时不时会有一两辆汽车拼命按着喇叭,从人群中挤过去。载人的电车也夹在人群中间穿行着。所有的人都在忙着一天的生活,为填饱肚子而奋斗着。道路两旁林立着三四层高的楼房,四处插满旗帜,商店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酒楼师傅的手艺着实不错,生意也很好,厨房的大厨正忙着将一只一只的烤鸭、烤鸡上架、出炉,大家忙得只希望自己能长出三只手、四只手来。而这时的三毛却饿得两眼无神,无精打采,他一只手捂着早已饿得连吵闹力气都没有的干瘪的肚子,茫然地走在马路边上,他实在是没有了力气,只能慢慢悠悠,摇摇晃晃地在街上游荡着,至少这样可以节省一些体力。
在战乱年代,养家糊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没有人敢轻易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和机会,所有的酒家和饭馆都尽早开张了。大家早早起来,做好了吃的,只等天一亮,便忙碌着将所有的食物都取出来,摆放到橱窗里,希望用它诱人的卖相招徕更多的客人。大家都在忙碌着,没有人注意到橱窗外趴着一个豆丁大,头上只长了三根毛的孩子。他现在正在这家名叫“南美酒家”的饭馆的橱窗前停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橱窗里一个一个的铝方盒里摆着的烧鸡、香肠、火腿等许多好吃的东西。P1-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