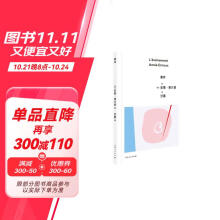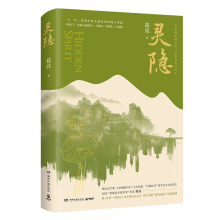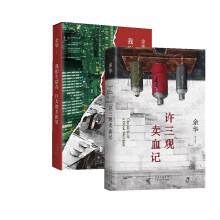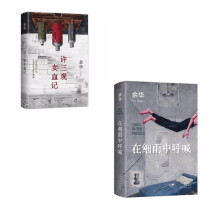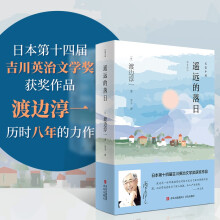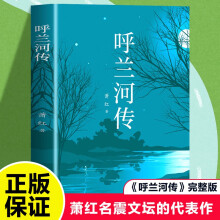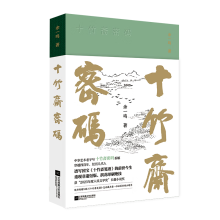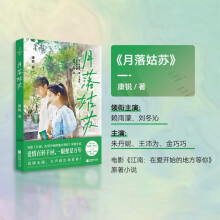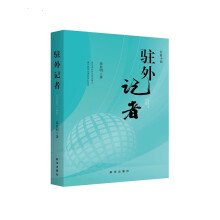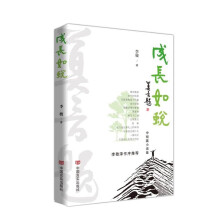《又是秋风乍起时/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陕西文学艺术创作百人计划书系》:
父亲年轻的时候买过好几枚金戒指,但没有一枚是戴在母亲手上的。我恨戴金戒指的每一个女人。在我幼小的心里,每一个戴金戒指的女人,都可能是我们家的情敌。
童年的记忆里,父亲身材修长,腰板挺直,精明、干练。他在就近的晋陕黄河两岸,分别开了四家染坊,这些染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永义和染坊”。其中位于我家上游二十里地隔河对岸山西克虎镇的染坊,规模最大,该染坊是父亲与他一位姓郭的结拜兄弟合伙开的。我叫父亲的结拜兄弟“拜老子”。拜老子和拜妈没有女儿,只有一个长我五岁的哥哥。有一年春节,在拜妈的再三邀请下,母亲带我乘渡船过了黄河,去小镇一起过年。身体虚弱的拜妈提早几天就为我们换洗了干净的被褥,当然也不忘为我准备了一件粉红色的小棉袄,作为见面的礼物。
拜妈常年哮喘,冬天更甚,每每咳嗽的时候,脸就憋得通红,而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及时踮起脚尖递上痰钵。拜妈好容易止住了咳,把带有血丝的痰吐入钵内,我接了痰钵很快跑出去倒掉,然后用半湿的沙土把痰钵擦拭干净,放回到离拜妈不远的地方备用,由此被一家人疼爱异常。
火炉上永远有一罐药咕嘟咕嘟地冒着棕色的气泡,药味四溢,我守在药罐前,学着拜老子的样子吹气、添柴、加火。我一点儿都不讨厌那味道,我的潜意识里知道,那是驱除拜妈病痛唯一的东西。拜老子用一根树枝拨拉着火炉旁堆成小山似的药渣,一一教我辨认半夏、竹茹、白花丹、天竹黄、洋金花、木蝴蝶等,很难理解这些拥有风情万种名字的花草,骨子里竟然都是苦的。
拜老子喜欢带我去南街的糖果铺买糖吃,一次只买两个,四分钱。一粒糖不舍得吮吸,只慢慢舔着吃,幸福便悠悠地延长了大半天。房檐下吊的冰溜子和火红的辣椒串以及那枚果味的糖粒,共同丰富了那个冬天的色彩。
父亲与拜老子情同手足,母亲和拜妈更是无话不谈。天气好的时候,拜妈就用棉花蘸了清油,抹在麻纸窗户上,原本暗白的麻纸,吸了油脂后,立刻变得像玻璃一样透亮。带着油香味道的暖暖阳光,不遗余力地照射进来,屋里顿时明媚了许多。两个女人在亮堂的屋子里,一边无休无止地捻着毛线,一边不厌其烦地说着比毛线还长的悄悄话。
几十年合伙生意,两家人从未因经济问题发生过口角,这也成了小镇上久久流传的佳话。这一定与背后这两个女人有很大的关系,拜妈和母亲从不掺和男人的事情,除了搞好后勤之外,两个女人甚至不过问一年的收成。
印象中的拜老子山羊胡子,温文尔雅,手里总持一把折扇,扇面上有彩色的花鸟,看书的时候,就戴一副水晶平光的圆框眼镜。拜老子写得一手好字,一纸、一砚、一笔、一墨,永远一丝不苟地摆放在门口干净且雕有精美云纹的案几上,以便随时记账。账本是线装的麻纸,每结清一笔欠账,就在名字下面画一小圆圈,每画一个小圆圈,拜老子眼角的鱼尾纹就活泼地跳跃一下。
我常常拽着拜老子的一角衣襟看他写字,每次写完,都不会忘记盖上砚台,以免墨汁变干。铜质发亮的砚台盖上,刻有一棵松树,树下是一位身着长袍的老者和一位挽着髻的儿童,儿童正在为老者指路,旁边配有一首诗。看不懂诗,只觉得那画有趣,便问拜老子,砚台上画的是什么?拜老子告诉我说,一个人去山里找他的朋友,可朋友没在。我问朋友去哪儿了?拜老子说,进山采药去了。我又问,这个人最后找到他的朋友了吗?拜老子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马上脆弱地想,要是采药的朋友遇到狼怎么办?还有那位身着长袍的老者,跑了好远好远的路来找朋友,若是再也见不着了,他会是多么的伤心啊!拜老子说我是小人儿精,想得太多了,也许是那个人在山里迷路了呢,说不定过一会儿就会回来的。而我的担心依然不减,我的杞人之忧是,倘若迷路在相反的方向,那不是越走越远永远都不能回家了吗?
晚饭吃得很少,我为可能永远都不能回家的朋友悲悲切切。
直到许多年之后,才知道那砚台上的文字是唐代诗人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那年春节,小镇闹秧歌、唱社戏,十分红火。父亲是方圆百十里地出了名的“伞头”,自然就成了秧歌队里的核心和领军人物。小镇对于他,早已不再是过客,而是归人。我挤进人群,只见父亲迈着细碎的步子,旋转着挂满了红缨的花伞引场子,流星般轻盈滑动,方寸不乱。上百人跟在他的身后轻舞飞扬,于表演中走五花八门的复杂阵图。远远看去,五彩的秧歌队就像是开在大地上一朵会流动的花,而父亲就是花蕊。父亲最经典的阵图有,里外十二莲灯、蛇盘九颗蛋、天地牌子、枣骨子乱开花、三鱼一只眼、千里一朵云等等。我常常想,父亲的心里一定有一张会动的图谱为他引路,因为这些阵图对于常人,别说是表演了,就是照着双手画,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其实,引场子远远不是父亲的绝活,父亲一生最绝的才艺是他出口成章的本领,随时随地,触景生情,房檐下藏的老母鸡,墙头上蹲的花狸猫;路过的马帮,穿梭的船队;驻足的商贩,飞翔的雁阵;枝头的小鸟,窗户的贴花等,都能巧妙且风趣地编入他的唱词,听得人连连叫好。他就像太阳吸引向日葵那样,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
唱秧歌是一个优秀伞头必备的技能,除自己担任主唱之外,队员们哪一个唱到一半若是忘了词,你得以最快的速度无缝地接住继续唱完。父亲“拾歌”的超强能力,总能赢得雷鸣般的掌声。
春节排门子唱秧歌时,“掉地上”(忘词)被看作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主家会很忌讳,唱者也更自责。但只要有父亲在,从来没有让秧歌“掉地上”的情形出现,所以无论组织者还是唱者本人,父亲在时,人人心里踏实。
“水萝卜自古皮外红,秧歌从古唱到今;扁豆生来一条根,困难就怕咱一条心。”这是我能记住父亲唱过成千上万秧歌中的其中一首,比兴、押韵,且充满了正能量。
其实,父亲的文化程度,仅仅够他作为一个平凡的俗人而不至于求人写字,但在我的心里,他是可以归于艺人一类的。倘若他的文化再高一点儿,那就是角儿。
父亲说他只读过两年冬书,学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和《百家姓》,他上学的时间加起来,统共不超过半年,可我惊异于他敏捷的思维和超强的空间想象力。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