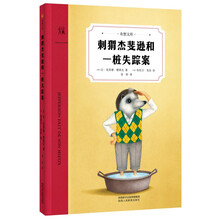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对啦,还有个男孩哦。”阿爸又对我讲。
“有多大?”正教阿丑衔棍子的我,忙问道。
“没看清呢。”阿爸拍打着棉衣,抱歉地说。
“那你和他说话了吗?”
灯光跳到阿爸的脸上,使得他的眉眼都笑笑的:“隔着野塘呢。”
我后悔只顾和阿丑玩,没和阿爸一起去采桑了。如果我在,一定要看清他长什么样,问他多大年龄,是扎灯匠爷爷家的亲戚,还是采药人的孩子。村里长着狗脊、天门冬、板蓝根,冬天采最好了。
睡觉前,阿妈照例要我用冬桑、茄秆和生姜熬的水烫脚。阿爸说,咱布谷村的人一年四季脸膛红彤彤,身体好,都是冬天脚烫得好。阿妈也说,烫脚,烫脚,当吃补药。
我每晚都烫得龇牙咧嘴,映在墙上的影子像在受刑。可烫完后,从脚心到心窝窝都热乎乎的,舒服得很。然后,再往被窝一钻,就像一下钻在太阳晒得暄腾腾的麦垛里,困得要死。可这晚,我好一阵都睡不着。
村里好久都没来陌生人了。
赶鸭人、养蜂人、卖货郎、照相的……不管谁来,我们都稀罕,都想要套近乎,都喜欢看他们干活,恨不得帮着赶赶鸭子,挑挑担子。如果他们还带着孩子,特别是男孩时,那就更好了。
前年夏天,赶鸭的老爷爷就带着他的小孙子呢。那男孩和我们一样大,当天就玩熟。我们带他粘蝉、偷瓜、翻地瓜泡、打弹弓,他则教我们做响响,又找来黄泥教我们捏猪八戒、孙悟空。我们还在草地上玩翻跟头、斗鸡。
早盼着再来个男孩。
阿妈讲,就是外面来头驴,我都会凑上去和它玩。唉,阿妈不懂。
一觉醒来,到处都是细细碎碎的声音,早起鸭子扑翅的声音,鸡刨食的声音,阿妈阿爸的低语声、脚步声。慢慢地,又像商量好,所有声音都沉下去,只听到露珠滴落的声音。我裹着棉被,掀开窗,一瞧,和昨天一样,下霜了。
站在院里的橘树,像给撤了层白白的糖霜,一只只小金橘的脸变得有点儿粉了。 一股调皮的霜风趁我不备,从窗隙钻进,直往我的脖里灌——哎呀,好冷。真想裹紧被窝,继续睡。
不行,不行,有一件事,昨晚已和自己说好。
和往天一样,阿爸站在院里的石缸旁,捧着个大茶缸,正喝着热腾腾的姜茶。
“怎么不睡了?”
“有事。”
阿爸的脸被热气抬起,狐疑地瞅我。
我忙躲到厨房。
阿妈已做好胡辣汤。喝上几口后,手啊脚啊才像彻底醒了。
阿爸阿妈商量谁去卖山货时,我去后院挖了蚯蚓,又找出小桶,将它挂在鱼竿上,扛着,像个奔赴战场的小兵,雄赳赳地出了门。
院外,种着梨树、李树和桃树,经过它们,就是我家菜园,走过去,再往前十多步,拐过一道月牙形的小弯,就是黑勺家。 我以为他还没起床,没想到他正蹲在院中长满杂草的磨盘上,捧着个大海碗,稀里呼噜地喝面片汤。
“知道不,扎灯匠爷爷家住进了人,听说还来了个男孩呢。”我装着漫不经心地讲。
“真的?”
“我阿爸说的。”
“可我答应阿妈,和她去看外婆。”
“哦。”
“会是什么人呢?”
“肯定是采药人。”
他也赞同。天这么冷,除了他们,谁会这时来布谷村?
“你要去钓鱼?”
我心虚地点头。原本是想和他、虫泥、胖弟一起去的,但我哪等得及。
不仅有霜,还有冰,路边的一棵棵杂草,变成了一只只冰刺猬,扫一脚,硬邦邦的,咔嚓咔嚓响。被它们簇拥的那些野菊花,一些已枯萎,一些还在热热闹闹地开呢,小小的、金黄的花,被寒霜冻出了药草味儿,一路蔓延至垭口的黄葛树下。在那儿,分出了三条路:右边通往布谷庙,中间通往淡香镇,左边通往扁担坡。
扁担坡不像扁担,像个斜斜的帽面。春天时,铺满山坡的蒲公英、打碗花、火棘、野蔷薇、狗尾草、锯齿草,这时已全进入冬眠,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丛鸡槭,逞能站着。坡顶平坦,像个狭长形的小操场,从坡的另一边往下看,一处灰墙黑瓦房,一个野塘,一块荒地,一片芭茅,两条羊肠小路,几块四散的水田,没有人。
是已经出去采药了吗? 我有些泄气,扛着的钓竿顿时变得沉沉的,但仍硬着头皮,沿着右边的小路,下到野塘。
野塘的对面,一溜排杂树后,就是扎灯匠爷爷家。和布谷村别家一样,院旁栽着一丛竹林,院前种着桃树、梨树和柳树。现在,它们都光秃秃地擎着乱枝乱丫,瞅着我,让我看不清遮掩在它们背后的门是开是关。
真的有男孩住进那里吗?我闷闷地想,捡了石头,往塘里砸。
“咔嚓——咕咚——”
“咔嚓——咕咚——”
P2-6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