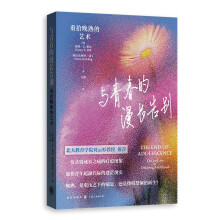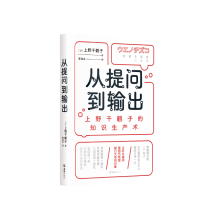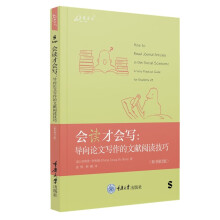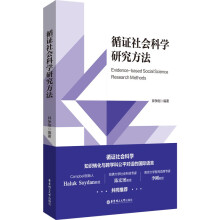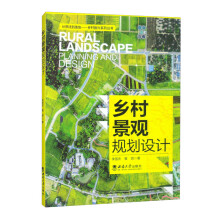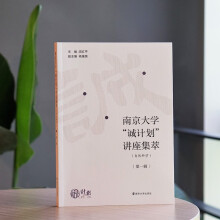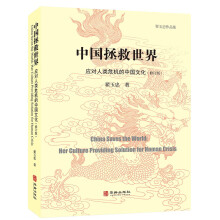《瑞羽:一个边汉社会的组织、仪式与认同》:
如果运用弗里德曼构建的宗族类型A和Z来观察,那么鲍屯的鲍氏宗族无疑属于Z类型,而其他杂姓则属于A类型。关于A类型,弗里德曼说:“宗族类型A的宗族成员比较少,大约只有二三百号人。除了一两位小店主和一些手艺人之外,宗族成员都是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民,其中有些自己完全占有土地,有些则是向外面的地主承租土地。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下。除了开基祖墓地所在的一小块土地之外,他们没有公共财产。人口增长产生的资源压力使他们无法婚配、没有后代,或者为了做工、做小生意不得不向外移民、入赘到一个陌生的村落,或者当兵和为匪。为了使自己免受其他宗族的攻击和侮辱,调解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们将自己置于强大宗族的控制之下;因为这种保护,他们必须以服务和纳税为代价。除了家庭的祖先崇拜以及在宗族开基祖坟墓前举行的年度仪式之外,没有其他的祖先崇拜仪式。没有族谱的记载,个人仅仅根据他们的代际置于系统之中,而且他们属于一个或者其他房,他们的源头从开基祖的儿子开始算起。房与家户之间没有谱系的单位,不存在联系亲密的家户形成经济和仪式合作之群体的趋势。这些单位中辈分最高、年龄最长者担任房长和族长的职务,并没有公认的其他正式领导者。纠纷由房长和族长处理,但当他们不能解决的时候,对自己进行保护的社区中的绅士便试图就此达成一个解决的办法。”①而关于Z类型,弗里德曼的说法则是:“宗族类型Z大约有两三千人口,在他们当中有退休的官员、官宦的家庭、待职的绅士。也有一些富商、一定比例的小商人和手艺人,以及大量的农民,他们当中大部分耕种以宗族或者宗族的许多裂变单位为名义掌管的土地。宗族成员的大部分是贫穷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宗族在土地、祠堂以及其他诸如碾米厂之类的财产是共同的。人们往往待在社区内部,因此,即使他们为了求官或者为了经商而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他们会寄钱回家,当他们年迈的时候则返回家乡。祠堂具有等级,但没有系统化;也即是说,有些房在祠堂方面其裂变现象比其他房更严重,而一个房的其他支以同样的方式比其他支裂变得更严重。这种非系统化与宗族中具有高级地位和财富的成员的不平等分配相契合。在这一系统中,族谱是重要的部分,连接着宗族与其他宗族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带来荣誉和有用的联合,而且显示了拥有财产的裂变单位的成员。在祠堂定期举行的祖先崇拜仪式表达了某一裂变群体的存在,与此同时,通过祖先灵牌的分离和祭祀者的区分,强调了社区中的地位差异。与类型A-样,族长是推举出来的,但是他们的位置处于绅士的阴影之下,这些绅士得到富商的赞助,对宗族事务进行集中管理。”①
以上较为完整地引述了弗里德曼对宗族类型A和Z的界定与论述,目的是将鲍屯的大小宗族与之进行比较。弗里德曼对宗族类型A和Z的界定,无疑是一个理想类型,与现实中的宗族类型并不完全一一对应。对此,弗里德曼也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已经讨论了宗族的A和Z模式。两者都不是对一种我已经能够考察的类型中所有宗族的平均的陈述。假如我们能够研究极端的个案,我们应该发现它们更多的是我想象的特点之概括。”①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鲍屯的大小宗族与A和Z类型所包含的指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就A类型来说,鲍屯的各个非鲍姓人口比较少,不到一千人。各个非鲍姓都没有祠堂。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鲍屯自古而今仅有鲍氏建有自己的祠堂,因此通常以家里的神龛和坟墓祭祖为主。但有一点相异之处是,鲍屯各个非鲍姓没有产生房支裂变,正如上文所揭示的情况。其他方面由于资料的缺失,无法进行比较,但情况可能依然是有同有异。就Z类型来说,鲍氏人口已达到两千人以上,并有房支裂变。历史上有宗族的公共土地和财产,有完整和连续的族谱。据说,族人之中也出现过官员。但仅有代表整个宗族的一个祠堂,各房支没有自己的单独祠堂。为了化解理想类型和现实的不一致,将多种可能性皆纳入他的理论框架中,弗里德曼又提出了中间过渡状态M类型,他说道:“假如我构建一种折中的模式M,它是模式A和模式Z的过渡模式,我们实际上可能更接近于普遍的历史事实。”②依此标准,根据鲍屯大小宗族的实际情形,我们可以将之定位在过渡模式M,但又是接近于分别处于两极的A和Z的模式M。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