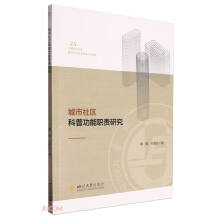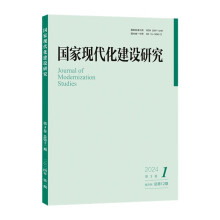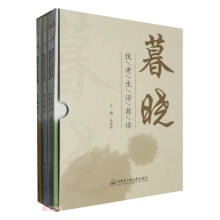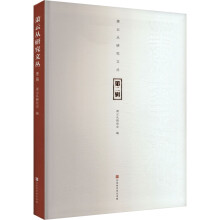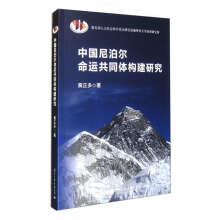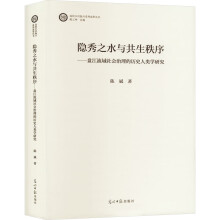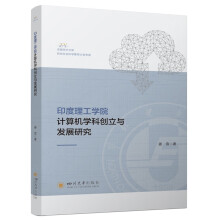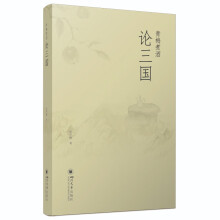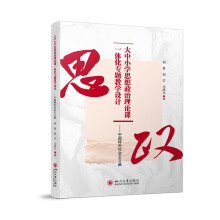《现象学视域下中西方面子观会通研究》:
其次,采访者的困境。据上所述,采访者两难处境不言而喻。采访者不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要求对方必须据实以告,更不可能严刑逼供,何况逼出来的也不一定是事实。这么一来,采访者似乎只有委曲求全,听凭对方言说。但是,最令采访者头疼的是,对方哪里撒谎了,哪个地方添枝加叶了,哪个地方过度阐释了,哪个地方矫枉过正了,都很难知道。同时,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了解对方,彻底地洞察对方心里每一刻的波动。基于上述论证,即便是最亲的人,你也不可能体验他所经历的所有事情,我们不能百分百断定依某人的习惯,他处理某件事必定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有不少研究者常常凭自己的经验判断熟识的受访者之所以在某件事的陈述中和平常其行为方式相悖,是因为对方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进行相应的掩饰乃至撒谎。试问,每个人都必须依据自己惯常的行为方式处理每件事情吗?如果受访者的行为动机都按照研究者的思维模式来进行,那么采访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采访的目的仅在于验证研究者的预设吗?是故,采访者面对受访者的“正当防卫”常常是“黔驴技穷”,有研究者认为可以用事后验证法知道对方是否真的在某个问题上撒谎。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受访者在访谈中提到自己在路上碰到前面的人身上东西掉了,自己会主动捡起并上前还给对方,那么我们可以在采访结束后不久叫某个受访者不认识的人在受访者平时路过的地方表演这个情景,看受访者有什么反应,检测受访者的诚信度。这或许是个好的方法,但是这有时也非常难以说明问题。受访者完全有可能在受访的时候告诉采访者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但采访结束后他在网上看到社会上有人利用这种伎俩来针对捡东西的人进行诈骗,那么他可能接下来碰见这种情况就有所警惕了,而这个原因研究者事先可能并不知道,那么对方如果在事后的验证中不按照其受访时所说的去做,就可以断定对方不讲信用吗?究竟该怎样去判断对方的诚信度呢?退一万步讲,即使研究者可以采用上述方法进行补台,难道研究者可能针对每个受访者说的每句话都来一次“事后证伪”吗?因此,采访者面对受访者解决其困境的自卫行为即便能做出预判,但难以完全清除受访者做手脚的蛛丝马迹,也就很难保证所获资料的客观真实性,面对这种情形,采访者为了自圆其说,就不得不凭借文化背景、个人经历、对受访者情况的道听途说对零散的资料进行整合,说得难听点,就是“添油加醋”。而依托所谓大的文化背景,我们总能对某些具体的行为差别做出解释,一定程度上也抹去了材料来源“伪”的嫌疑,而实质上是研究者凭借其主观臆测却仍不能阐述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而迫不得已的办法。
最后,采访本身的困境。叙说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假设前面两个困境都不存在(尽管这种假设在现实中根本不成立),即受访者完全相信自己的受访资料不会被除自己和采访者以外的第三方知道,对采访者的任何提问都据实以答,而采访者也完全确信受访者是不会欺骗自己的,双方在采访的前后达到完全互信的理想状态,那么我们一起来讨论采访这个活动本身的问题,这个困境从根本上是非常难克服的。为什么呢?
因为深入采访涉及思维的一种基本行为——反思或者说在回忆中反思自己过去的经历。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事后诸葛亮”,即便是一种回忆,也不可能是一种当场的经验,如此一来,在采访者事先有预谋地、深思熟虑地设计出的采访提纲引导下,当事人在彼时彼刻的述说和其本人之前经历的事实本身是否会存在出入,笔者想这个问题绝对是不容小觑的。在西方现代哲学史上,这个问题曾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转折点。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是20世纪反思现象学的创始人。但是新康德主义者那托普(Natorp)(1854-1924)对胡塞尔的反思现象学提出了两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攻击,可以说直接击中了胡塞尔理论的软肋。第一个挑战是,“你认为现象学是在反思中进行的,通过反思描述原本的生活体验,但是,因为有了反思,使得生活经验不再被活生生地体验着,而是被观看着了。也就是说,你的反思止住了体验的流动,使得被体验的东西成为某种比较固定的对象。……所以你的反思止住了体验的流动,这样现象学描述的东西就不是原本的流动之中的体验”。举个例子说,昨天你因为朋友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把你放在桌子上的书拿去看了,结果导致你昨晚要写论文找不到书,你昨晚因此特别生气,还和朋友在电话里理论了一番。今天,别人问你昨天那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反思一遍,当时是如何如何愤怒,本来是很愤怒的事情,被你这么一反思,你现在还愤怒吗?或者说,你现在的愤怒还是昨天的那种愤怒吗?同理,你昨天觉得很丢面子的事情,今天再回忆起来还会觉得丢面子吗?我们知道,丢面子这个东西是随情境而定,也许你昨天当场确实感觉很丢人,但是你昨晚回到家一想,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是捡了大便宜,今天重新回忆时可能就变成称赞自己很有面子了。换句话说,反思或回忆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真的是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要打问号的。第二个挑战是,“那托普认为,胡塞尔还要用语言对这种体验进行描述,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描述、任何语言表达,都是一种普遍化和抽象化,所以根本不存在一种直接的描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