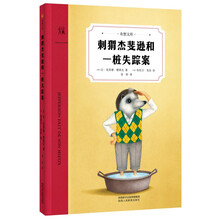拽住妈妈衣襟
小时候,上街是一件愉快的事,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我刚懂事时,上街由妈妈抱着,不愿走路而旋颈展望四外风景,而且我的视点与妈妈的眼睛同高。小孩子总是希望居高眺望。在妈妈怀里逛街,还有一个好处是困了便睡,越颠簸睡得越香,涎水淌湿母亲肩膀。那时我当然不知道妈妈是否辛苦。
及长,上街被妈妈用手牵着。她一手牵一个,那边是我姐姐。“那边”即右边,我喜欢待在妈妈左边,即“这边”。倘若妈妈买了东西,先松开姐姐,右手持物。如果买了个西瓜,她双手捧着,我和姐姐就同时拽着妈妈的衣襟。
拽着妈妈的衣襟遍览街景,是人生最可钟情的回忆之一。小孩子手拽着母亲衣襟,眼睛却向四外看,脚下踉跄着,在我小时候,吾乡赤峰街景单纯,目光飞快者三两眼即可掠尽。然而我们并不像大人那样浮躁,只看商店与楼房。天上白云舒卷,如苍狗骆驼可观。某处古屋房檐长草可观。卖肉的手起刀落,油手将带血的牛腱子肉掷入秤盘可观。蛐蛐儿声不知从何而来可观。卖糖人儿的老头手捏孙悟空可观。书店在三道街口,门前矗一龙门(或牌坊)。走到那里,我总仰望龙门,心里想小鲤鱼试图翻越的情景,它太高了,小鲤鱼真可怜。一路上总是这样跌跌撞撞的,从繁华的三道街回到我家的箭亭子家属院,装一脑袋混乱的印象入睡。
在街上,我拽着妈妈的衣襟习惯了,倘拽不到,手举着空落落的。我不知道自己那时候有多高,一举手刚好到妈妈腰间,扯住她的后衣襟。
前几曰,陪我妈妈上街,发现她身高连我肩部尚不够。那么,我小时拽她衣襟尚须伸手,彼时我何等小巧玲珑,而且会走会动,能记住这么多往事。现在,陪父母上街,他们全听我的意见,诸事无不诺诺。我真是不太愿意,他们像我小时候一样无须动脑筋了。我长大了,其实我早长大了,只是在知道拽着母亲的衣襟上街这种愿望已永远不能实现时,感到“长大"的惊痛。
在我印象中,我母亲年轻时常穿一件暗绿色带花的右衽衣裳,即被我无数次在后边拽过的。我问过妈妈,那件衣裳呢?她平静答曰:“谁知道。”这说明一切的确久远了。
人长大了真不知有什么用处,特别是我,对社会和别人无所供益,只是徒然闯入中年。《二十四孝图》中的老莱子年及花甲,尚穿彩衣躺在父母怀里撒娇。除了“孝道”之外,这行状难以卒睹。或许他想返回童年,但童年已被岁月的砖石密密麻麻地砌死了,如同我不可能拽着妈妈的衣襟上街,如同赤峰街里早就变样,如同一切都变样了。
不久前,我看到两位老人散步。跨越马路牙子时,男人用手扶老太太一把。一看,这是娘俩儿。儿子已白发苍苍,母亲逾八十岁,仍装束整洁。老母亲在儿子扶她的时候,目不斜视。我看了很感动。
在我老了而母亲更老的时候,她上台阶时,我应不失时机地扶一把。我所能做的,大约只是这些了。
照片和木梳掠走的时光
我爸在报社工作时,请摄影记者到家里照相(但记者更愿意说他是在摄影)。我家因此比别人家多出一些黑白照片,镶在镜框里。
摄影记者叫杨义,他三十多岁就叼一支烟斗,细眼,脸常带笑容。被杨义摄影要具备胆略,他左手高举闪光灯:“别动!"低头看莱卡相机的取景框:“别喘气!"杨义眼睛眯得愈细,愈表示他真的要摄影了。啪!闪光灯爆响,炫目之光直取人面。
我们每次都吓一跳,脸可能都吓白了。闪光灯爆裂的声音很大,它用短路的方法放射照相需要的一丈光芒。杨义微笑着,关上莱卡相机厚厚的皮盖,叼起烟斗,我爸划火柴替他点烟斗。
照相时,杨义让我们笑:“就像我这样。"他嘻嘻笑着。我不知道(现在也没弄明白)照相为什么要笑。我家照相之际,窗玻璃上堆满向屋里张望的脸庞,大人或小孩的脸。他们严肃地、惊奇地观看照相或摄影的全过程,而我们竟在笑,其实连哭的心都有了。闪光灯啪地爆响后,窗外趴着的人逃走一多半,我姐吓得钻进挂蓝花布帘的高桌底下,我爸用手攥住炕沿。我照相时被闪光灯吓到,留下惊魂之态。杨义说:“你看,浪费一张胶片。”其实,笑这个事真不是说笑就笑的,我们后来才渐渐会笑。我们对闪光灯大骇之际,杨义很满意,他不知看过多少张被闪光灯吓坏的脸。
杨义给我家留下不少照片,我妈看《人民画报》、我姐跳舞、我穿灯芯绒小褂举纸旗抗议美国出兵巴拿马时都有照片,我们都在笑。但我们还是不愿照相,一来闪光灯可怕,二来笑更可怕,三来要回答家属院里小孩、老婆子的咨询:“照相疼吗?腿抽筋吗?"没办法。
我爸常常不征得我们同意就把杨义请到家里,我们略微表示不想照相,我爸立刻大发脾气,摘帽子摔在桌上,咬牙、出汗并擦汗。杨义理解我爸的心情,哄我们把相照上。那时候,照相(对不起,摄影),特别是照生活照并不容易。P1-11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