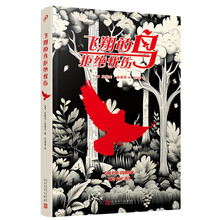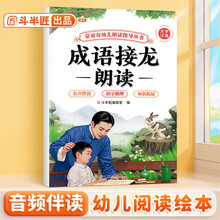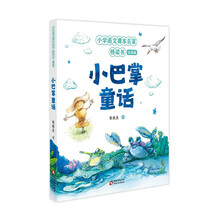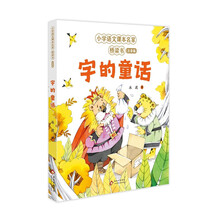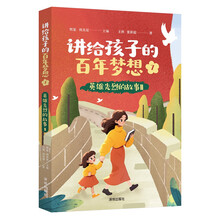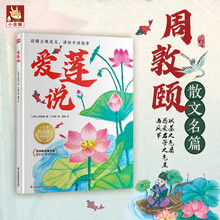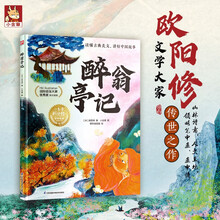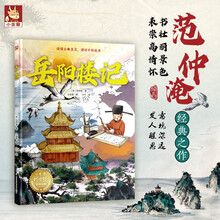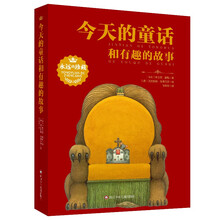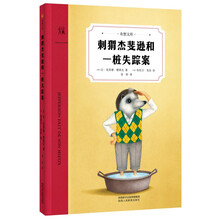《高门楼儿(大字版)-黄蓓佳童眸系列》:
下午放学回到家,朵儿被弯弯纠缠着给他折个纸兔子,刚折好,拿红蜡笔画上兔子的眼睛,还没来得及把身子吹开,卫南啪嗒啪嗒地跑过来,拉了朵儿就走。
“快快快,闻老爹家来了个乡下小孩,听说是他抱来的孙子……不不,是给他儿子抱的儿子……哎哟我也说不清楚啦,我们去看看吧。”
卫南就是这么个虚促鬼,做什么事情都是慌慌张张没个准头。其实闻老爹家要抱养个小孩的事情,朵儿早就知道了,而且还知道闻家抱养的这个小孩子,是闻老爹的侄孙,就是他兄弟的孙子。闻老爹的儿子闻叔叔没有小孩,闻叔叔的乡下堂兄弟小孩子又太多,好像有六七个,都不知道凭一点工分口粮如何养大,就大大方方给了闻家一个。
准确地说,这不叫“抱养”,叫“过继”。这是朵儿听好婆说的。好婆又是听居委会杨主任说的。闻家过继了乡下小孩,要在城里上户口,所以要找杨主任开证明,所以杨主任对这事一清二楚。
朵儿家住着的这条仁字巷,有横竖两条,横的一条南北向,竖的一条东西向,两条巷子呈“丁”字形状,交汇的这一点,就是闻老爹的家。精确一点说,闻老爹家算是竖仁字巷的人。高门楼子是他家的特征。随便哪一个人,从南大街拐进仁字巷,头一眼看见的,肯定是闻老爹家那个华丽气派的门楼儿。不仅仅是门洞高大,门口有两个光溜溜的石鼓模样的础石,还因为门檐翘得像鹿角那么神气,门檐下面镶着的水磨大青砖上有各种各样的雕刻,像蝙蝠啦,石榴啦,还有什么法海水漫金山,张生月夜翻墙……仔细看的话,每块砖头都在说一个从前的故事。可惜前几年闹红卫兵,那些戴着红袖套的小将们蹬着梯子爬上去,硬是拿凿子凿个乱七八糟,叫个什么“破四旧”。好婆一提这事,就要皱眉咂嘴痛心疾首:“好好的东西,真作孽!”
住在高门楼子里的闻老爹,要算是仁字巷里最有学问的人。从前他教私塾,家里开了课堂,堂屋里从早到晚书声琅琅。后来青阳城解放,私塾不准再办了,闻老爹就参加工作,当了小学老师。再后来他退休,有一份退休工资,闲时帮不识字的街坊们写几封家信,年底给巷子里每户人家写副对联,日子过得还算闲适。
朵儿看过闻老爹帮人家写信,开头总是这样:“××我儿:见字如面。”下面就是家长里短七七八八的事情。最后再来一句:“余不赘述,就此搁笔。母嘱。”文绉绉的话,古里古气,好笑得很。
朵儿在闻老爹家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帮他扯着长长的红纸条,看他写对联。墨汁在砚台里磨得又黑又浓,油汪汪的,散发出很醉人的香味。闻老爹拈笔,蘸墨,手捋着胡须沉思片刻,先来一副:“春归大地人间暖,福降神州喜临门”,横幅是“福喜盈门”。再来一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楼”,横幅上写“四季长安”。
对联贴到门上,居委会杨主任走过来,背着手,一副副地审查。他指着“岁月”的那个“岁”字,皱眉:“我说闻老爹,怎么是繁体字呢?”闻老爹恭恭敬敬答:“报告政府,繁体字写着好看,畅快。”杨主任骂他:“真是个老顽固!写繁体字是复辟,这你不懂?等着挨批啊?还有,你看你写的这些对子,福啊,寿啊,乾坤啊,封建意味很浓啊。”闻老爹吓坏了,吓得脸都发白了,一个劲儿地检讨:“错了,错了,我重写!”
回家就重写。不敢写那些复杂的字句了,写副最简单的,毛主席诗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横幅“欢度佳节”。这个最保险,永远都不会有人挑错。
……
展开